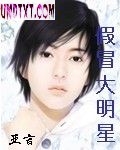梦回大明十二年-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瞬间福华如遭雷击,过去了这般久的时间,她竟然还清晰的记得那晚的情景,她怔怔的喃语道,“你。。。你就是那个水晶桥下穿素白衣裳的女子。。。居然是你,居然是你。。。”
那一夜,她提着玉兰花灯,携手着一身挚爱的男子姗姗额笑语而行。身处闹市里,亦如在一场甜蜜沉醉的美梦中,那大抵是她这一世人生幸福的顶点吧,却不想就是那夜,一切幸福都注定是梦幻泡影,她绝望的闭上了眼睛,颤抖道,“三哥从前那般疼我爱我,都是因为你。要是没有你,我该过的多么幸福。”
不提防忽然有一个声音在旁冷冷的说道,“你若不是因为长得像她,又怎会真的取代我姐姐,成为裕王正妃。你本身就是个替代品罢了,要是我说,你还得谢谢她才是。”这话说得刻薄而又毒辣,嫣儿正是攀着石壁,一边喘着气,一边解恨的说话。
“住嘴!”福华大喝一声,面色苍白。其实她心中早已知道这话也许都是真的,只是从来不愿意去相信。此时她只觉得自己腹中泊泊的血在往外涌,她心知这腹中的孩子必然是没了。一时间诸般绝望、苦痛涌上心来,那必是爱恨滋味纠结,她挣扎了一下,竟然猛的站了起来,去捡起了那本悬翦剑向安媛扑了过去。安媛哪里有防备,向后踉跄几步却逃不开,一旁的嫣儿站的最近,见状猛然推了安媛一把,让她避了开去。
福华眼见刺不到安媛,剑锋忽然一转,又向嫣儿猛然刺去。
悬翦剑气最凛冽,眼见剑要及人,嫣儿只觉得一阵寒气铺面而来,她这一下却无路可退了。福华这一下是用尽了力气贯出的,她无论如何也躲不开了,她心下一凉,闭目只待受死。
“嫣儿。。。。。。”耳边是安媛带着哭腔的吼声。嫣儿心中忽然略有完满,至少前一瞬,她并不后悔。
一只手堪堪拦在了嫣儿面前。
那剑果然是宝剑,刺入骨肉竟然一点声响也无,就已然贯掌而过。嫣儿睁开眼时,只见张居正面色苍白的站在面前,正是他伸出掌来拦住了长剑,竟是用一只肉掌生生受去了这一剑之力。
福华贯出了长剑,早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又一次摔倒在地,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只是回头恨恨的望着安媛,用尽残力道,“我生来必是与你相克,我好恨,我好恨。。。。。。”她转过头去,亦是恨恨的望向嫣儿,神色凄厉道,“还有你,我也恨。若不是认识了你,我这半生大抵也不会如此度过。。。。。。”
她喃喃的低语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忽然她用尽全身力气,坐直了身子,头一偏向一旁的石壁上撞去。只听猛然一声惨烈的声音,已是血溅石壁,香消玉陨。
过了许久,嫣儿方才从震惊中转醒过来,她回过头去,直望着张居正,忽而说道,“张先生,谢谢你救我。”眸中光影朦胧,点点跃金。
“适才你推开了她,说明你尚还存一点良知,”他捡起了地上染血的悬翦剑,缓缓插还鞘中,他因手上受了伤,只能用左手握剑,那右手就闲闲的垂在袍下,殷红的血迹刺得嫣儿目中灼痛,“值此之后,我们师徒之间的恩怨,就都是两清了。”
嫣儿心中一痛,如梦初醒,她缓缓地扫了一眼眼前的人,眼中蓄着泪,却竭力不能落下,只是含着笑道,“好,好。。。。。。”
她默了一瞬,又是良久,涩然问道,“先生,以后将去哪里?”
“去哪里,我便陪她去哪里。”他低头望了望怀里的女子,沉吟了片刻,柔声问道,“你说去哪里?”
“离开,离开这个地方。。。。。。”安媛仿佛刚从这血腥中回过神来,望着地上福华全成一团的尸首,身子依然有些颤抖,“嫣儿,你随我们一起走吧。”
嫣儿望着他们,却摇了摇头,目光中有几分复杂,“我不走。。。。。。我还有着皇妃的身份,好歹也会无事的。堂堂一位王妃死在这里,也还有许多事需要料理。。。。。。再说,再说天下之大,我还有哪里可以安家呢?”
说道后来,她的声音愈来愈小,仿佛是在自问,又仿佛是在伤感。
。。。。。。
一青一素,两个身影,转眼绕过一个山口,已是去得远了。
嫣儿依旧呆呆的伫立在原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喉头一甜,嘴角溢出几缕血丝。
从皇陵一路下山,山路甚是崎岖难行,不过转过了几个山弯,便连先前巍峨磅礴的宫室也看不到了。才走过一个山口,却瞧见有一个锦衣卫装扮的侍卫站在路旁,隔得远了看不起面目,只瞧见身后还有几匹马。张居正募然全身戒备起来,右手便按上了腰间的悬翦剑。谁知身旁的安媛忽然止住了脚步,怔一怔神,猛然向前奔了几步,却搂住了那个小侍卫,唤道,“如松,你怎么会再这里?”
张居正这才注意到,那侍卫身材矮小,看上去约莫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却不正是镇守辽东的挚友李成梁的长子李如松。如松如今脱去了稚气,穿上了锦衣卫的服饰,却也显得很是精神,只见他本神色紧张的张皇四顾,此刻见到了安媛,却喜形于色,叫道,“姑姑,可算等到你了。”他又看了一眼安媛身旁的张居正,略一愣神,赶紧恭恭敬敬的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唤道,“恩师。”
张居正轻轻点了点头,却道,“恩,起来吧。”
安媛又惊又喜,拉着如松问道,“你何时拜他为师了?”
如松脸上露出一点羞涩的神情,说道,“半个月前,在爹爹的营帐中恰好看到张先生挥剑克敌的情形,心中很是敬仰,便拜先生为师学习剑法。爹爹也是极力支持呢。”
“你爹爹···”安媛听了听如松的话有些意外,回头看了一眼张居正,轻声问道,“你和李成梁将军见过面了?”
张居正不动声色的点点头,神色里有些不自然,“见过一次,在军营里。”他亦是沉思了一瞬,却皱眉向如松问道,“你为何会在这里等安姑娘?”
如松有些迷茫的抬起头,奇道,“恩师,不是你给如松留的字条,要如松备好三匹良马,就守在这里等待姑姑的么?”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薄薄的精美笺纸,上面隐约有两行小字:
“如松吾途,申时备良马三匹,侯于京郊十八道岭西路山口,以待为师。切切务误。
师启”
安媛凑过去瞅了一眼 ,只见纸笺上的字都是一般大小,笔记圆滑娴熟,正是张居正的一笔端正的小楷,她也不免“咦” 了一声。
张居正轻轻瞥了一眼,却道,“学的甚像,只是我从来不用十竹斋的笺纸。”
如松呆呆的看着手里握着的笺纸,只见上面浮着淡淡的山水墨迹,纸质匀薄而华美,笺纸底端更有饾版浅青竹画,一看便知价格不菲,果然不是素喜简朴的老师所用的,他嗫嚅道,“恩师,恩师···”却半天接不出后文。
安媛见如松神色沮丧,不免对着张居正一笑解围道,“我瞧这寄信的人也没存什么坏心,让如松在这里等我们,还送了几匹马来,更加节省脚力。至于学你的字迹···约莫是相熟的人写的。不过是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如松,你挑的这匹马倒是很精神。”
如松果然闻言轻松了许多,赶紧牵了马来让安媛看。安媛见他选的马匹都是高头大马,模样漂亮,看起来就甚是精神,更不免刻意称赞了几句。如松一讲起马来就来劲,说道这匹全身白色不含一根杂毛的叫做夜光白。这匹浑身乌云墨黑,唯有四蹄雪白,乃是相马谱上赫赫有名的乌云盖雪;另有一匹通体都是血红色泽的正是相传自大宛来的“血汗马”‘这匹匹都是名驹,乃是如松专门从大内御马监里精心挑出来的。
如松把“血汗马”牵给了安媛,说道,“红儿性子最温顺了,适合姑姑坐骑。”又把“乌云盖雪”恭恭敬敬的牵给了张居正,低声道,“师父,请您试骑。”
张居正仔细瞧了瞧那匹马,脸色却沉了下来,眉目中隐隐有不悦之色,“远途奔走,短小精瘦的马屁方有长力。这些马匹虽然生的高大,模样漂亮,兴许从前会有名驹的血统。但却是从小生活在御马监中,吃着最上等的饲料,从未出过远门。我们走的是山路,这些马匹难免会踩到石子,崴伤了马蹄,骑乘最是危 3ǔωω。cōm险的。这便如同出身优越的高门子弟,自小富贵,然而华而不实,耐不了久力,便没有多大出息吧。”
如松顿时泄了气,很是愁眉苦脸的悄悄抬眼望着安媛。想不到张居正竟然是这样一位严师,对学生时刻敲打,很是苛责。如松生性活泼跳脱,李成梁有意让他拜这样一位严师,恐怕是为了磨磨他的性子的。安媛心中暗暗好笑,口中却道,“甚是,甚是···”
如松间没了撑腰的,只得讪讪的低下头去,含了委屈小声道,“恩师,如松知错了···”
张居正面上没有半丝表情,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望了望天色,说道,“走吧。”
三个人各自牵了马缓步下山,此时天色渐暮,无尽的晚风吹来,微微蕴着一丝凉意,枝头的半黄的叶间渐渐吐了些新绿,卷着一点点未化尽的霜雪,彷佛蕴有了无限的生机。
行了许久,只觉得身在连绵起伏的山势中,仍未有走出去的迹象。安媛只是称奇,“这里的山真是大,走来走去像迷宫一样。”
张居正心中募然一惊,止步问如松道,“你今日几时牵马来的?”
“纸笺上说申时要到,弟子辰时初刻便出发了,”李如松迷惑不解的望着张居正问道,“恩师,可是有什么不对么?”他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叫道,“糟了,我们怕是走错路了。”
安媛不觉愕然,“我们不是从你来的道路走出去的么?”如松又是羞愧又是悔恨的说道,“姑姑,我是辰时出发的,从京城到皇陵少则需要两个时辰,而从官道进山的路至多不用一个时辰就可到了。可眼见如今太阳西斜,怕是戊时都过了,别说走出去,我们就连官道的影子也望不着,那必然是走到岔路上了。
张居正点点头,抬头望了望夕阳一点点躲到云层后,叹了口气说道,“十八道岭地势复杂,没了阳光指引更是难行。今日怕是走不出去了,不如就在此地将就歇息一宿,待明日太阳出来了再走出去。”
安媛暂且安了心,围着火堆烤着火,眼见着如松不一会儿便把周围的四个火堆都燃了起来,浓炽的火光映的黑夜亦有黯然红色,远远瞧来恰似围成了个火圈,果然看上去安全了不少。
张居正见生好了火,便远远绕着火堆查看了一遭。待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却多提了几个物体,看上去似乎是活物,只是黑夜里瞅不清楚。如松到底是小孩心性,冲过去看了一瞬,兴高采烈的对安媛叫道,“姑姑,晚上有烤兔子吃了。”
如松一边说着,一边麻利的从腰间掏出了一把错金小倭刀,开始剥洗内脏。安媛瞧着那刀在黑夜中寒芒极盛,倒似是一柄利刃,销筋断骨如同销泥一般,不免多看了几眼,赞道,“真是柄好刀。”
如松略一怔,将刀反转递给安媛看,笑道,“是啊,这是爹爹多年贴身之物,这次如松出门前,爹爹去哈密卫平定叛乱了,特意把这柄刀留给孩儿带着的。”
“哈密卫”安媛略一愣神,“你爹爹不是戍卫嘉峪关。”
“姑姑在宫里消息真的闭塞,自姑姑走后,我爹爹就升职做了副总兵。今年入春以来,天山北路的瓦剌多番来扰边关,我爹便出兵去镇守,如今已在哈密卫了。”
“成梁将军昔日,曾用此宝刃助我脱过困境,”张居正从旁边略看了一眼安媛手里玩赏的小倭刀,淡淡开口道,“十多年前,我因恰好往辽东去,那时候是冬天,建州一代匪徒出没甚多,我便孤身遇到了一群匪徒,那帮悍匪武功尚可,仗着人多,不容分说便一刀砍下了我骑乘马首,迫我下马来。然而语言又不通,只听他们激骂叫喝,困得我一时不得脱围。”
安媛虽然与张居正认识许久,却还是第一次听他提起当年遇困的旧事。张居正的武功她是见识过的,十余个锦衣卫高手相围,他数招便能解脱,况且招式狠辣,好不容情,寻常歹徒哪里奈何的了他。此时听他提起当年的一群“悍匪”,虽然轻描淡写,想来却足以让人生畏,她不免心下一颤,下意识的一抖,错金小倭刀便“铛”的一声掉到了地上,身子亦微微发起抖来。
张居正知她关心,微微握了握她的手,以示宽慰,一边却捡起了那刀,续道,“那时我第一次遇到李成梁将军。他正巧独自路过此地,见我受困,便大声以当地语言喝问那些悍匪。对方高傲的很,似在斥责他多管闲事,李成梁兄大怒之下,忽然间揉身下马,以一极薄的利刃直取匪首,震慑群匪。那时他用的便是这把宝刃。”他说着将这刀上的血迹轻轻在袍角擦进,递还给如松,当地说道,“你爹爹将这刀送给你,除却望你有利刃防身,也有盼你成才之意。”
如松听得两眼放光,小心翼翼的接过这把刀,他听到父亲与师父当年同力克敌的往事,不免心生向往,满脸都是羡慕之色。
却听张居正譫然地望着远处,彷佛想起了许多往事,低声的叹道,“你爹爹当年与我相识之时,一见如故,遂成八拜之交。那时如松还在嫂嫂的肚里···”
如松正在兴奋之中,全然没有听到。安媛却在旁听得清楚,她募然想起李成梁的夫人当年却是为了生如松难产而亡,这许多年来李成梁再未娶妻,想来也是对这位先夫人有太深的伉俪之情,而当年为李夫人救治的也是张居正,想来他是见过如松生母的。她斜向张居正望去,只见他的面上投上了重重的阴影,更显得目色深沉。
三个人围着火堆闲闲的趣话,夜色不知不觉深了。如松用树枝串了剥洗干净的兔肉在火堆上烤,不一会儿便有脂香四溢,香味扑鼻。如松迫不及待的就去撕下火堆上的烤肉,却烫的手猛的一缩。安媛急忙道,“可慢着些,这火上多烫啊。”
如松只是皮赖的笑,伸手撕下了一条后腿,拿桂叶包了递给安媛道,“姑姑快尝尝,新烤出来的最香了。”说着他又从怀里摸出一块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皮质的东西来,一并递给了安媛道,“姑姑吃的时候,拿这个在肉上擦一擦,味道更香。”
“这是什么?”安媛有些疑惑的接过,却很是怀疑,她把那东西放在鼻尖闻了闻,隐隐只闻到一股孜然的香味。
“那是盐孜,”张居正亦接过了如松恭恭敬敬递来的一只兔腿,却笑着瞥了一眼安媛手里的东西,淡然说道,“宫里的锦衣卫多半是世家的儿郎,平日里骄纵皮赖惯了,常随御驾护卫斋戒,没了肉食,便会去百姓家偷鸡摸狗的烤了吃,荒郊野外哪里有作料。他们便想出了这个法子,把盐巴和孜然用高火煮成块,吃肉的时候只需要擦一擦,就很鲜美了。”
安媛且惊愕且笑,于是拿了那盐孜然、擦了擦兔肉,再入口咀嚼,果然油腻解了不少,肉味更加鲜嫩,竟是难得的美味。她不由笑道,“这群猴精的小子,怪不得宫里的宠犬都养不久,平白惹了她伤心了几日,原来都是进了你们的肚里。”
如松讪讪的笑着,拿了块烤的喷香的兔肉咬了一大口,却说道,“师父真是英明,徒儿什么都瞒不过师父去。”
三人笑着说了会话,眼见着天色越来越暗,有厚重的铅云堆积,渐渐的连天畔的星星
也看不清了。如松到底是个孩子,吃饱了聊了会儿便有了困意,慢慢就靠着一块大石头睡了去。安媛怕他受惊,便拿了长衣替他盖上。
“你对这孩子,倒是很上心,”他清朗的面上半带着微笑,凝视着她的双眸说道,“这孩子也是与你来的亲近。”
安媛侧了头,瞧着如松的面上满是温柔神色,“这孩子从小丧母,很是可怜,又叫了我一声姑姑,难免多怜他几分。他年纪还小,你和成···李将军都对他太过严苛了。”
“玉不琢不成器。”张居正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话语却很简促。黯然的火光在他脸上隐隐投下了几分亮色,也很快被他的蕴藉的沉郁之气收了去。安媛嘴唇微微动了动,却没有吱声。张居正觉得自己过苛了些,温言道,“我瞧着你对孩童都很亲近,若有孩子,你定然是个好母亲。”
没来由的心中一痛,安媛的面色暗了暗,想起了早逝的玲儿,不免抬头向山上望去,远处依稀的灯火处,该是永陵的扩大宫室。铃儿如今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地下,该是很冷清了。顷刻间她的泪水忍不住涌出,温热的模糊了视线。
似是有人轻轻在背后环住了她,她觉得自己落到一个温暖的怀抱中。她忍住泪,只静静地望着远方,却听见耳边传来低沉的呼吸声,浮动了她鬓边的一缕发梢,“别哭了。以后,我们有个自己的孩子吧···”
她的心须臾间有那么一瞬的颤抖,似乎是在寂静的暗夜里放逐漂泊,终于却泊到了一个避风的港湾,竟是一种为不可知的温情慢慢包围了她。
冷冷的寒风吹来,夹杂着山间微凉的秋意,地上的火光忽明忽灭,大有一种凄寒鬼魅的重影。山间无月,笼重的寒意慢慢袭来,激得她白皙的皮肤上起了一阵寒栗。他似是觉得了怀里人的冷了,又紧了紧怀抱,温柔的握住了她冰凉的手,看到她苍白的脸色很是心疼,“冷了么?”
安媛低头轻轻嗯了一声,却不说话。
张居正耐心的等了许久,瞧见她单薄的身形在寒风中如吹不尽的愁绪,却并无开口的意思,心下又是一叹,却道,“你想去哪里走走?尽管说出来,我现下也无事了,天涯海角都陪你去吧。”
“我并无想去的地方,”她忽然轻声开了口,长长的睫毛扑扇着如轻盈的蛾翅,“我在想适才嫣儿的话,天下之大,真没我容身的地方。”
“怎么会这么想……,有你在的地方,我都会在的。”他迅速的抬起头,柔声化解道,“你不是曾经说想去江南走走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个时节去是最好的……,或者我们还可以去金陵转转,那是我朝的开国之都,自古繁华不输京城,再有苏杭景致,都是天下奇妙绝佳的,山水宜人,也适合久住,便隐于市间做个陶朱公也不错呵。”
有你在的地方,我都会在的。他的声音轻柔却坚定,有那么一瞬,她心里被绮恋充满,抬起头来痴痴的望着面前的人,看着他薄薄的嘴唇上下翻动,仿佛是一道利剑刻在心上,她极力的抑制住身体的颤抖,半眯着眼,徐徐温婉的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