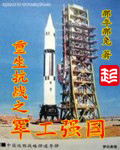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绝世风光-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倪采记得她。上辈子,就是这个女人想方设法嫁给了骆嘉树,断送了骆嘉树的音乐前程,而后竟生下了别的男人的孩子,让骆嘉树颜面扫地。
她唇色鲜艳,肤白如雪,一头充满光泽的栗色大鬈发垂于肩上,虽是东方面孔,却溢满了异域风情。
张艺茹微笑着朝她二人走来,骆嘉树神色如常,从容淡定。
忽然间,他感到臂弯中的手臂紧紧缠绕了过来。倪采将身边的男人拉近了自己,她紧紧靠在骆嘉树身侧,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骆嘉树心下暗笑,竟觉得她万分可爱。
“这位是?”
“她是倪采,我的女伴。”
“倪小姐,你好。”张艺茹朝倪采伸出右手,倪采只好将手从男人臂弯中抽了出来,同张艺茹握了握。
刚刚的不适已经消失,倪采冷静下来,忍不住嘲笑自己:太奇怪了,那么紧张干什么。
骆嘉树朝人群一瞥,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揽过倪采的肩膀,抱歉道:“不好意思,艺茹,我和倪采先失陪了。”
说完,牵起倪采便往角落走去,留下张艺茹一人咬牙切齿,又不好发作。
第8章 逢场作戏()
r8逢场作戏
“jenkin';yarin。”
拥抱之后,骆嘉树拍拍这位与他年纪相仿的男人,笑着为倪采介绍:
“季言思,我在麻省理工的同学,言思,这是倪采。”
季言思看到骆嘉树女伴的一霎,眼睛亮了亮:
“jekins,眼光不错哦。”后又转向倪采,“倪小姐,你好,我是季言思。”
猜测到他俩亲密的关系,倪采礼貌地率先伸出手,没想到这位海归公子捧起她的手放到唇边吻了一下。
骆嘉树故作不耐地推了季言思一把,问道:
“别四处放电了,你那位呢,不是说今年带回来见见?”
季言思终于正经起来,环顾四周,答道:“她还没到呢,应该快了。”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成功?”
季言思白了骆嘉树一眼:“你不懂,这叫慢慢来,比较快。”
“哈哈,什么道理。”
兄弟俩谈笑风生之时,寿星出场了。
薛林保先生上台说了几句话,下来后立即被上前恭维的人团团围住。
随老先生一同到场的几个年轻人中,一位米色裙装的姑娘尤为出众。她不言不语地跟在薛林保身后,偶尔温和地笑笑,同身边人交谈几句。
“喏,她来了。”季言思一下子精神许多,“我带你们过去认识认识。”
他们三人结伴走到那位佳人身边,季言思向她介绍了骆嘉树与倪采,尤为殷勤。
季言思的心上人,正是今日寿星薛林保的亲孙女,名为薛蕾,今年刚毕业回国。
她真是水一般的人儿,温婉恬静,身如弱柳扶风,实在惹人怜爱。
倪采只在一旁看着他们三人交谈,鲜少插嘴,她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阶层不同,无需多言。
季言思拉着薛蕾去往别处,这儿又只剩倪采与骆嘉树两人。
宴会大厅中想与骆嘉树搭话的人很多,可他总礼貌地回复两三句,毫无热情,其他人每每自觉尴尬,便不再叨扰。
闲来无事,倪采也不好四处张望,她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季言思和薛蕾身上,任凭超能力挥发。
一看不打紧,看了,倪采更觉心中不是滋味。
季言思是真把薛蕾放在了心上,两人面对面站着,薛蕾身旁满是名为“季言思的爱”的粉色光晕。而季言思呢,除去别人给予的乱七八糟的颜色,此时他身边最为显眼的,竟然是一片焦土之色。
棕色,意为不屑。
季言思在薛蕾眼中,不过是她嗤之以鼻的存在。既然这样,她脸上那温柔似水的神情又是怎么回事?
“倪采,你看什么呢?”
骆嘉树的声音拉回了倪采的思绪。
“没什么,随便看看。”
“是不是宴会太无聊了?”
“没有没有,只是。。。。。。有点感慨,季言思那么喜欢薛蕾,可薛蕾没能回报同等的感情。”
“哦,这你能看出来?”
倪采摇了摇头,道:“女人的直觉。”
在骆嘉树看来,倪采不是一个只凭直觉就妄下推断的人。
说不出为什么,每当他看向倪采那双深潭般美丽而深邃的眼眸时,总觉得心头微颤,好像只消一眼,他的过去与未来,便全在她的眼中了。
被团团围绕的除了寿星,还有一位身价更高的亿万老总。
骆骏正和身边的总裁们讨论着明年的商会项目,眼神却时不时瞥向另一头的骆嘉树那边。
他这个别人眼中才华横溢、聪明绝顶的独子,作为父亲的他却一点也看不透。还有,他身边那个美丽的女伴,骆骏也从未听他说起过。
骆嘉树这个孩子,总在费尽心思地,一步一步想要脱离他的掌控。
宴会结束后,骆嘉树送倪采回了家。
他绅士十足地先下车为倪采打开车门,倪采怪不好意思的,扯了扯裙摆,寻思着如何同他告别。
“谢谢你,我美丽的女伴。”他眨了眨眼,那双眼中盛满星光,引人失足深陷。
“不用谢,我也算长了见识。”
耳边有风吹过,拂起倪采脸畔的细发,她勾起唇角,低声道,“那我先走了。”
“嗯。”骆嘉树微微点头,却伸手按住了倪采的双臂。
“嗯?”
倪采疑惑地抬头,几秒后,又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屏住呼吸。
浅浅的一吻落在她的额头上,骆嘉树的唇瓣柔软、微凉,如秋夜的露水,如振翅的蝶翼,在她战栗的肌肤上轻扫而过。
倪采睁大了眼睛,两辈子,除了父亲以外,从没其他男人亲吻过她,即便是额头。
她那副惊恐的表情落在骆嘉树眼里,几乎惹得他失笑。
只见骆嘉树抿着下唇,眼角蹦出细细的笑纹,他原就生得俊美无匹,更兼这副宠溺姿态,直把倪采看呆了去。
骆嘉树松开了她,声色温润:“倪采,再见。”
“再,再见。”她口齿不清地回应道,急忙转过身,踩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冲进了楼里。
骆嘉树回到车里,敛去了刚才的所有表情。
“先生,回家吗?”
他摇摇头:“thedanuberiver。”
二十分钟后,这辆奢华的黑色轿车驶进了市中心一处地下停车场。骆嘉树乘坐电梯上了楼,电梯停在一层名为“thedanuberiver多瑙河酒吧”的楼层。
“怎么样,再来一局?”
骆嘉树耸耸肩,离开台球桌,坐在这间独立台球室的吧台边上,为自己倒了一杯清酒。
“你真是越来越没意思了。”季言思只好放下手里的球杆,坐到了他的身边。
骆嘉树伸出自己骨节分明,白皙匀长的手,笑道:“怕手酸,明天还要练琴。”
“少爷您真金贵,要不要小的给您捶捶?”
“无聊。”
季言思倒了杯伏特加,一口喝掉一半:
“那我们聊点有趣的。你今晚带的女伴真不错,特有味道。”
“那是自然。”
“哟呵,瞧把你乐的。”季言思把酒杯随便一放,“你那张大小姐对你那么上心,又该怎么伺候?”
骆嘉树眼神晦暗不明,道:“她是她,我是我,没什么干系。”
“可你看她今天那眼神,只差把倪采生吞活剥了。”季言思来了兴趣,“肯定气着了。”
“那又如何?倪采生得讨喜,聪明又知进退,丝毫不倨傲,比她好上千百倍。”
而且,在倪采淡定自若的外表下,还装着尤为单纯的一颗心。
季言思禁不住“啧啧”两声:“骆嘉树,你该不会真喜欢上倪采了吧,你小子行啊!”
骆嘉树皱起眉心,举起手边的高脚杯再啜饮一口。他没做多少思量便摇了摇头,道:
“没有,我只是受不了张艺茹罢了。”
季言思递来一个“你这是欺骗小姑娘感情”的眼神,没再多言。
几年前,两人一起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多少女生见了骆嘉树便忍不住投怀送抱,比倪采更聪明、更漂亮的女生比比皆是,可骆嘉树除了皱起眉毛,绝不会有更多回应。
后来,他离开麻省理工改学音乐,又成了首屈一指的钢琴家,别看他表面上温润如玉,内心却比钢铁还要冰冷坚硬,凭倪采这点道行,恐怕真不能撼动分毫。
可怜我们的倪小姐,只能沦为骆音乐家击退烂桃花的工具了。
11月12日晚,洗漱完毕的倪采躺上床,拨了个电话给林新月。
大半个月的相安无事没让她放松一丝一毫,和母亲通话,顺带探些于叔叔的消息成了每日例行。
“哎,妈妈,没有啦,我今天一点也不累。”寒暄了几句,倪采又开始旁敲侧击,“妈,你今天有和于叔叔见面吗?”
“你最近怎么回事,这么关心于叔叔,都不管你妈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的感情生活吗?”
电话那头的林新月忍不住笑了。
最近大半月,她总觉得女儿懂事了不少,曾经那个只会埋着头念书,什么也不愿过问的倪采改变了,她由衷地感到高兴。
“噢,我前两天听你于叔叔提过,他好像明天一早要出趟差。。。。。。”
“什么,他要出差?”倪采不禁握紧了手机,“妈,你怎么今天才告诉我!”
林新月不解:“之前忘了啊,你凶什么。”
“不是,那。。。。。。你知道于叔叔去哪吗?”
“知道,去美国,那地儿叫什么来着,好像是洛杉矶。”
倪采猛的舒了一口气。
天哪,她牵肠挂肚大半月,难道之前一直都猜测错了,其实于叔叔真的去了大洋彼岸,母亲身边的颜色才会。。。。。。
可是,好像又有什么地方说不通。。。。。。
“妈,于叔叔明早就走啊,几点呢?”
“这我怎么知道?应该挺早的,听他说,在禄石机场搭的春季航班。”
“噢。”
倪采应了一声,电光火石间,脑中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闪过。
她沉默着闭上眼努力回想,睁开眼时,心脏狂跳,一口气差点喘不上来:
“妈,你确定,是明早飞往洛杉矶的春季航班吗?”
“是啊。。。。。。小采,你的声音怎么了?”
“妈,我有点急事,先挂了噢。”
她也察觉到自己声音喑哑,双手发颤,急忙结束通话,又翻开手机通讯录,拨出另一个号码。
于叔叔,快接电话啊!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她再拨一次,话筒里依旧是那冰冷的人工提示音。
倪采挂了电话,飞快换掉一身睡衣。
她跑到阳台往外边望了望,大都市繁华缤纷依旧,可天公不作美,泛着夜晚红光的浓云已渐渐压了下来。
第9章 迷失神志()
r9迷失神志
倪采挂了电话,飞快换掉一身睡衣。
她跑到阳台往外边望了望,大都市繁华缤纷依旧,可天公不作美,泛着夜晚红光的浓云已渐渐压了下来。
倪采取了一把伞,刚走到门口,又折回卧室一屁股坐在了床边。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什么对策也没有,就这么贸然跑到于叔叔家里,她什么也做不了。
难道让她直接告诉于成海:
我是重生的,我知道明天,也就是11月13日的早晨,宁州禄石机场唯一那班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春季航班sh810,将在太平洋洋面上空遭遇强大对流天气,机翼及发动机损毁后坠入大洋,全机上百人,无一人生还?
倪采再次闭上眼睛,飞快做着各种各样的假设。
她站了起来,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只能这么办了。
倪采走进厨房,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保温盒。很快,她便关上房门,离开了小区。
“叮咚叮咚。”
门铃突然响起,一时无人回应,门外的人又着急地按了几下。
“谁啊,这么晚了。”
于成海咕哝了一句,从衣柜里找了件外套披上,他扫了一眼电视上显示的时间,都快九点了。
“来了来了。”
见来人不停按着门铃,于成海从屋里大声回应道,跑出来对着猫眼看了看,急忙开了门。
“于叔叔。”
“倪采?怎么这么迟还过来啊?”
倪采白着一张脸,手里拎着保温盒。
她走进客厅,将保温盒放在桌上,道:
“还不是我妈,晚上多熬了点粥,非要我给您送来。”
于成海疑惑道:“她住得离我那么近,怎么还叫你送啊?”
“我下了班就去她那儿了,没事的,回家也顺路。”
于成海坐到倪采面前。原本听新月说她这个女儿性子偏冷,不好亲近,可认识了大半月,他觉得倪采对自己很热情,算得上关照有加。
这样最好,他可以更放心地同新月交往了。
“女孩子家的,大晚上还是不要乱跑。”于成海将一杯温热的开水推到倪采面前,“你妈也真是的,难道一点不担心?”
倪采握住桌上的玻璃杯,心中泛起涩涩的暖意。
多少年了,她有多少年没有体会过父亲的关爱了?她忍不住偷瞄一眼于叔叔,只觉得他的面目愈发慈祥,心下更为坚定:
我一定要救他!
“于叔叔,你快趁热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毕竟是妈妈的一片心意。”
“哎,好勒。”
他从厨房里拿了碗筷,满满倒了一碗,心满意足地品尝起来。
在他示意倪采也舀一碗时,倪采摇了摇头,只坐在一边静静看着他。
对不起了,于叔叔。
来小区的路上,她先去饭馆买了养生粥,又去药店买了半瓶安眠药。
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倪采往粥里扔下两片安眠药,苦恼了好一会,担心剂量不够的倪采又往粥里加了四片。
这样即使闹钟在耳边响半个小时,于成海也醒不过来了。
六片安眠药,是安全服药的极限,有可能对人体造成一点损伤,但顶多醒来后头疼几小时就没事了。
整整三碗,于成海吃得一干二净。
又闲话几句,他将保温盒还给倪采,送她到了门口。
“倪采。。。。。。”于成海忽然打了个哈欠,“叔叔送送你。”
“不用啦,我自己走下去就成。”
“还是我送你吧。”说完,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哈欠。
倪采连连摆手:“您看起来很困,还是早点回房歇息吧。”
将于成海劝进了卧室,倪采独自下了楼。她松了一口气,可心里愈发难受起来。
这就是成为预言家的代价吗?
她好想现在就打车冲到机场,用尽一切办法阻止明天的航班;她好想找到所有乘客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地劝说他们改签;她好想。。。。。。可她除了能救回于叔叔,其他事情,依旧无能为力。
倪采拦了辆车,打算回家。
她逼着自己不去想,这不是她的职责,她又不是救世主。。。。。。
她不可能暴露自己重生的身份,即使她愿意暴露,会有人相信吗?他们只会认为她是个疯子。
多少条鲜活的生命,即将消逝在远离故乡、无依无靠的海面上。
倪采的心依旧钝痛,她朝窗外扫了一眼,雨点一滴一滴落在玻璃上,愈下愈大,模糊了整片视野。
前方是一片霓虹闪烁,马上要经过钻石大剧院了,倪采在宣传广告上看过,今天似乎有一场歌剧上演。
她盯着窗户上汇聚、滴落的雨水,再次感叹这世界的无情。
“司机,停车!”
倪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塞了过去,打开车门便跳下车。
车外大雨滂沱,她却全然不顾。
“姑娘,还没找钱呢!姑娘,你的伞!”
倪采已经跑远,司机师傅等了一会,还是无奈地开走了。
刚才在车里,透过雨水铺就的光影,她看到一个熟悉的、早已铭刻进心底的面孔。
他叫多吉巴桑,是一个藏族男子,他的脸很有特点,倪采确信自己不会认错。
上辈子,就是这个善良而悲悯的男人,帮助她逃出了异能研究所。
多吉巴桑也是个拥有超能力的人,他比倪采早几年被骗进异能研究所,在倪采来之前就逃走了。
之后的几年里,他一直没离开宁州,担心被研究所的人找到,他不停地更换住址。
多吉巴桑不愿离开宁州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想救出还关在研究所里的伙伴,却只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旦倚靠外界的组织,例如政府官员、司法机关,除了打草惊蛇,甚至有可能危害所里的同伴。
他第一个救出,也是唯一一个救出的人,便是倪采。
在层层雨幕中,倪采分明看到多吉桑巴正走在钻石大剧院旁的街道上,可当她拨开人群冲到那处时,他早已不见踪影。
倪采疯了似的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心中的无奈、痛苦、不甘,还有激动,通通乱作一团。
冰凉的雨水落在她的身上,浸湿她的衣襟,淋湿她的长发,却也折磨着她的心智。
举着伞的路人纷纷绕开她,倪采全身都湿透了,依旧没有冷静下来。
“多吉巴桑!多吉巴桑!”
没有人回应,他已经走远了吧。
倪采站直了身子,双手抱住脑袋。
我不是全好了吗?可这种感觉是什么?!!
倪采全身的血液好似都冻住了。
这个缠绕她两年的梦魇再次找上门来,她战栗着,费力地想要保持清醒。
我不要再抑郁了!
不知不觉,眼角的泪滴已顺着雨水滑落。
骆嘉树举着伞,从剧院后门走到了前门。
歌剧《蝴蝶夫人》的第一场演出刚刚谢幕,室外雨如倾盆,街道上的人丝毫不见少。
人行道上,一个衣着单薄,完全暴露在雨水中的女人异常显眼。
她脸色惨白,双眼茫然,骆嘉树对上她的目光时,心蓦地一缩。
“倪采,你怎么了?”
头顶上多了一把大伞,倪采无助的抬眼一望,喃喃道:
“骆嘉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