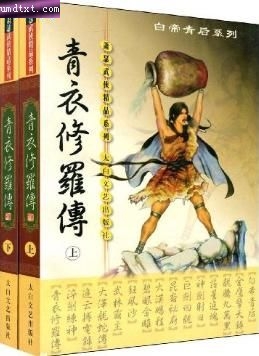高衙内新传-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卢员外客气了,这认人小事,举手可办,只是这人被救之后口中常说些胡话,小生也听不清楚,好似什么茶呀马的,不知贵府总管可还有这等营生么?”高强悠悠地道。
卢俊义脸色不变:“草民家中食口浩繁谋生不易,倒也有些盐茶马羊的营生,日常都是这李固掌管帐目,似衙内这般说,更象了,还望容草民一观。”反正梁中书是默许他的走私生意的,承认也无妨。
哪知高强却笑道:“哦,卢员外倒是财源广进哪,小生倒要讨教些生财之道,唉,东京城虽然百业兴旺,家父却是为官清廉,对小生又是管束甚严,平日实在是手头拮据,倘能学员外一般做些赚钱营生,这个,小生也过几日宽松日子了。”这就是明着开价了,你卢俊义要人可以,我高衙内就是认钱的,看着办罢。
卢俊义面色微变,偷眼看了梁中书一眼,却见这狗官端着杯茶,用盖碗一下一下地拨着浮面的茶叶沫,就象没听到他二人说话一样,心中暗骂了一声,脸上赔着苦笑道:“衙内过于抬举了,草民只不过走南闯北谋些糊口的米粮,哪里比得上衙内金马玉堂的富贵,况且近遭丧妻之痛,早无心弄什么营生了……”说着竟哽咽起来。
第二卷 河北 第一五章 转仕
卢俊义在这里哭穷,那是讨价还价的意思,高强自然心知肚明,既然事先已经定下了与其合作的方针,这当儿便要先把自己的价码开出来,让对方定下心来:“哦,卢员外近遭大丧,小生也是代员外难过,听说员外每年往来北地贩运盐茶,想必事务浩繁,小生有意与员外共行此事,俾可助员外一臂之力,也免得员外因丧劳神过度,不知员外意下如何?”这话说来已经甚为无耻了,人家刚死了老婆,你来谈什么合作?不过这等场面上话,听的都是潜台词,本衙内看上你的生意了,你做的什么生意大家心里也都有数,还是识相点好。
卢俊义听到“往来北地贩运盐茶”几个字,心中暗惊,偷眼看了一旁的梁中书,见他还是那副淡定模样,心下更惊,看来这位大名府留守相公是铁了心不管自己的事了,否则高衙内言下已经提到了自己的走私买卖,梁相公怎么也要说几句话,譬如“卢员外奉公守法,大名府百姓多仰赖其惠”之类的。
此刻对方手握铁证,而且人证物证俱全,倘若真要翻脸,除了指望梁中书代为斡旋以外别无他法,可看这位留守相公的样子,牢靠程度有限得很,卢俊义踌躇片刻,暗一咬牙,向高强道:“想草民一点微薄营生,能入高衙内的法眼,实乃三生有幸,只不知衙内想如何共行此事?”还是问一下价码吧,看看能不能谈。
高强暗喜,这已经上了路了:“卢员外既有此意,小生这里倒有个计较,想员外往日奔波劳苦,途中又多强梁猾吏之扰,行商殊为不易,不如小生上复家父,借我大宋殿前司军资转运的名义为员外顺手带些货物,员外只消付些运费便是。”看了看一旁的梁中书,又加了一句:“就交给大名府留守司充做军资便是,此乃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员外意下如何?”明知此事不可能绕开梁中书,索性做大方状,横竖自己和蔡京一系正是狼狈为奸的时候,这事又非借殿前司的名义不行,他梁中书总不能独吞吧?
卢俊义一听,这说的什么鬼话,刚才还说要一起做生意,转脸就利国利民了,谁信哪?可潜台词他还是听明白了,暗自盘算了一番,却觉并无多少损失。要知当时行商羁旅,最大的成本不是货物,而是路上的运输损耗,更多的则是沿路豪强和贪官污吏的勒索,各种买路钱、保护费等等不一而足。至于盗贼匪类之流倒不见得有多大威胁,毕竟玉麒麟“河北枪棒第一”的名号不是吃素的,倒有一多半是在绿林道上打出的名头。
如今若能在卢家商队插上“殿前司军资转运”的旗号,可想而知,不但盗匪望风披靡,各路大小豪强和官吏没一个敢伸手的,仅此一项每年就省钱不下二十万贯。而且除此之外,更可以调用御河兵船转运物资和银钱,运费又省下一大笔,实在是笔划算的买卖。——只除了一点,殿帅府要收多少保护费?
“衙内赤心为国,不愧是将门虎子,草民佩服之极,只是草民向在民间行商,却不知这军中运费几何?”
高强看了看梁中书,却又犯起嘀咕来了:这位梁世叔貌似是不会庇护卢俊义了,可如何分赃又成了问题,到底原先卢俊义给他上供多少,心里着实没个准数啊,罢了,还是问玉麒麟吧:“此事虽说是为国家,却不能要员外平白多些负担,小生敢问卢员外,原先每年运费几何?”说着向梁中书那边斜了斜眼睛。
卢员外场面上人,这等关节自然一点就透:“好教衙内得知,草民往日每年运费要用到二十万贯,倒有一半用在行商人众所食的粮上。”说到这个“粮”字时稍稍加重了点语气,又向梁中书那边斜了斜眼,显然“粮”就是“梁”了。
高强暗吃一惊,这位梁中书好大的胃口啊,难怪每年能给老丈人上供十万贯生辰纲,敢情咱卢大财主一年就要给他烧这么一炷高香啊,看这卢俊义的意思,是想给自己同等待遇了,如此也好,他梁中书等于没吃半点亏,一切照旧而已。
既然价码基本谈妥,也就可以请梁世叔表态了,高强转身笑道:“梁世叔,小侄这番粗浅的计较,您老可得看顾着些,免得小侄年幼无知,有甚行差踏错之处,堕了家父和世叔的名头。”
梁中书将手中茶杯一放,开口便笑:“贤侄为了朝廷如此尽心竭力,可知令尊大人家教甚严,贤侄不日即当平步青云,为我大宋的栋梁啊,愚叔自当看顾则个。”
他既然表了态,一桩交易就此尘埃落定,高强和卢俊义都是松了一口气,卢俊义便向高强道谢:“既然留守相公也这般说,草民能得为朝廷出力,都是拜留守相公和衙内所赐,自当铭记不忘,只是草民的生意往来多有仰仗总管李固之处,还望衙内请出相见。”
本以为这次没问题了,谁知高强又有新花样出炉了:“员外且休着忙,小生还有一事相询。那日在翠云楼饮酒之时,贵仆燕青按酒布菜,吹弹说唱,样样俱佳,生得又是仪表堂堂,真难为员外怎生寻得如此佳仆,小生在东京殿帅府的数十个帮闲没一个比得上的,不知员外可愿出让?”燕青是卢俊义家仆,按照大宋律例,须主家点头、本人亦同意方可买卖,因此要先问卢俊义的意见。
卢俊义闻言先是一怔,既而便有些要作色起来,旋即想起自身的处境,憋了一口气道:“衙内既然看得起我家小乙,草民自无不允,只要小乙点头便是。”原来燕青就在门外相候,卢俊义向梁中书和高强告了罪,转身出去,不一会便领了燕青进来。
几日不见,燕青瘦了许多,脸上没了往日春风和煦的笑容,显得沉默而抑郁,给梁中书和高强见礼时也是机械得很,浑不似以往那倜傥潇洒的模样。
高强知他心伤贾玉莲之逝,此刻正饱受煎熬,也不禁有些恻隐,便道:“小乙哥别来无恙?想必卢员外已经说了,小生极是敬佩小乙哥为人,盼望能朝夕相伴左右,不知小乙哥可愿相随?”
燕青默然片晌,回身向卢俊义拜了四拜道:“主人,小乙自小蒙主人收养,教以诗书,授以拳棒,名虽主仆,情同父子,平生只愿长随主人左右。今高衙内有心要小乙相随服侍,小乙但凭主人吩咐便了。”
高强一楞,本以为燕青在卢俊义身边经历了如此大变,必生求去之意,谁知竟还是这般忠心,实属难得可贵,卢俊义有这等人才而不能用,真是让人横生范增、田丰之叹。只是这想法在心头掠过,却更坚了他招纳之心,不等卢俊义答话,便开口笑道:“小乙哥忠心为主,小生佩服之极,只是小生当日火场中救出的那人,至今神智不清,整日胡言乱语,说什么违禁犯法的事务,却要小乙哥去认认,到底是不是贵府总管才是。”
此言既出,卢燕二人都是面色一变,高强这般说话,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卢俊义见高强本已谈好了交易,此刻却又来要挟,已按捺不住,亢声道:“衙内,草民情愿去指认那人,烦劳衙内相请便是。”
高强一脸的奸笑道:“卢员外此言差矣,那人在火场中受了惊吓,至今神智不清,谁都不得近身,只得关在内宅。试问员外如何进这留守司内宅?只除是小乙哥转作了小生家仆,这内宅方可进得,那人方可认得,这言语方可分辨得。”
卢俊义面色大变,回眼看了看梁中书,见这位相公竟还是稳坐钓鱼台,又回头看了看跪在眼前的燕青,神色变幻数次,终于长吁了一口气,颓然道:“小乙,衙内既这般说,你……你便随衙内去吧,脱籍文书回头便送到衙内手上便了。”
燕青霍然抬头,二目电光般在卢俊义脸上扫视一轮,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半个字来,只又磕了四个头,起身时竟似脚下有千钧之重,拖泥带水地跪在高强面前,还没磕下头去,已被高强抢上扶起,大笑道:“小乙哥,小生与你一见如故,今日后得能宾主相待,足慰平生啊,呵呵呵……”
“燕青愚鲁,蒙衙内错爱,敢不竭力奉仕。”生硬的话语,令人不敢相信是出自这风流伶俐的“浪子”之口。
“来来来,小生这便带你去看看那胡言乱语之人,认一认是不是贵府总管李固。”高强一手牵着燕青,向后堂便走。
过了半晌,二人复又出来,燕青脸上无半点表情,走到卢俊义身边躬身道:“卢员外,小乙已经仔细辨别过,那人不知是哪里来的妄人,决非李总管。”
停了一停,又道:“小乙揣测,李总管定是当日在翠云楼便葬身火海,尸骨无存了罢!”
听到“卢员外”这三个字从燕青口中说出,卢俊义已说不出半个字,只觉得眼前这张英俊无匹的面容,前所未有的遥远,陌生。
第二卷 河北 第一六章 奇案
眼看大事底定,梁中书打了个哈哈,正要说几句场面话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门外一个旗牌气喘吁吁地跑到门口,大声道:“禀留守相公,衙门前有人前来首告刀伤两命的血案一件,当案孔目请留守相公坐衙!”
梁中书吃了一惊,忙交代了几句言语,匆匆去了。这边留下高强和卢俊义、燕青三人相对,燕青是默然无语,卢俊义刚被高衙内敲诈了一番,却也没甚好气,只说要回去处理丧事,燕青的脱籍文书和细软家私随后命人送来,便出言告辞。
高强拉着燕青送到留守府外,燕青仍是无话,在大门口又磕了四个头,卢俊义只把袍袖一拂,便径去了。
二人恰待回身,却见人马摇动,军健喝道,梁中书换了官服,一群公人簇拥着出门来,见高强二人站在门首,便笑道:“贤侄,倘若无事,何不随愚叔去那血案现场,看看公人如何办差的?”
高强自然笑应了,却拉着燕青一同去。
一行到了东门内大街,早有地保等辈上来接着,引到一处僻巷所在,有一群小厮正在那里哄闹,见留守司的大队前来,轰的一声都散了,跑出几十步去又站住,远远地瞄着。
这群小厮一散,当中现出一片空场来,仵作公人不必梁中书号令,一拥上前去勘察现场,不一会便回来禀告:“回留守相公,今见地下男尸两具,俱都脱得精赤条条,乃是一个出家和尚,胸腹间中了刀伤四处,都是致命伤;一个头陀道人,喉间被利刃割断,一刀殒命,身边放着一口带血的解手尖刀,疑似凶器。地下还有一副糕粥挑子,一半已经打翻,米糕粥汤散落一地。余外并无所见,请留守相公明断。”
梁中书皱着眉头听完了,便叫带过一个老汉来,问道:“这老汉,地下这糕粥挑子可是你的么?还不将所有本末从实招来!”
两旁衙役旗牌齐声威吓,那老汉已是近六旬的人,这一下吃惊不小,脚底一软便跪在地上,只叫:“相公明断!小人实不曾杀人,冤枉啊!”
见不是头路,一旁早上来一个地保,陪着笑脸道:“回留守相公,这老儿是这片街坊常见的王老汉,每日清早出来卖些糕粥营生,街坊邻居多与他相熟。今日一大早小人等听他大声叫唤,又是一片乱响声,慌忙出来查看时,只见这老儿跌坐在地下,一副糕粥挑子打了半边,碗碟粥糜等物散碎了一地,中间一片血泊,躺着这两具尸首。小人等见出了人命官司,不敢怠慢,便叫同伴守着凶案现场,拉着这王老儿前来首告。”
他这一番说完,那王老汉也回过神来,忙道:“留守相公明鉴!小老儿日常只是摆布些糕粥营生,平素小心谨慎,连蚂蚁也不曾踩死一只。今日一早四更起来,走经这一条巷子,只因天色朦胧老眼昏花,不曾看下面道路,没提防绊了一跤,起来时见地下两个血人,惊得小老儿站立不稳,忙叫街坊邻居出来时,却被揪来见官,其实不曾见这两个,又哪里敢杀人!还望留守相公青天明镜,昭雪小老儿不白之冤!”
说着喊了几声冤,又哭丧着脸道:“这一跤跌倒,把些碗碟家私都打碎了,还不知以后如何营生,相公可怜见!”
梁中书忍不住好笑,旁边公人等也都忙凑趣笑了几声,高强在一边看了也觉有趣,这老儿喊冤实在是有些水平。
梁中书从旁边叫过一个孔目来,问他如何看法。那孔目姓木,五短身材,长得象个圆球,留了一道横排的小胡子,两个眼睛瞪得溜圆,过来给梁中书见了礼道:“禀相公,据小人看来,这两个都是出家人,与世无争,应当排除情杀和仇杀的可能,从尸体周围别无长物,连衣物都被剥去来看,当属谋财害命无疑。”
他话音刚落,旁边就出来一位,高高瘦瘦,留两撇小胡子,两只眼睛颇有色光,却也是一个孔目,乃是姓毛:“非也非也!禀知府相公,据小人看来,这两个虽说是出家人,然而那和尚下身颇有腥臊之味,且又不着片缕,颇似是做了什么有伤风化之事。况且,倘若是谋财害命,贼人连内衣鞋袜都不放过,那一把尖刀亦值得五七十文钱,为何却丢下了?”
梁中书听这毛孔目说得有理,刚点点头,那木孔目把小胡子一吹道:“毛老弟,这却有一件不妥之处,若说那和尚有伤风化,那头陀却也是精赤条条,下身又不闻有甚腥臊之味?老弟所言,欠通啊欠通。”这毛孔目与木孔目便你一言我一语,在梁中书面前讨论起案情来。
高强听得头晕,独个儿走到现场旁边观看一会,却摸不着头脑,忽听老远那群小厮唱词,随风飘过来几句,有什么“淫戒破时招杀报,因缘不爽分毫”,又有什么“大和尚今朝圆寂了,小和尚昨夜狂骚”,只觉得耳熟,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高强暗中寻思,自己到这古代未久,市井中也不大厮混,这样的小词并未听过几支,难道还是以前听过?脑筋就往水浒等书上去想,忽地省起一事来,忙叫过地保来问道:“这大名府外可有一座报恩寺么?”
那地保见他衣着华美,又与梁中书一路,当下不敢怠慢,恭敬道:“禀衙内,那报恩寺乃是本地第一座丛林,就在西门五里外,日常香火极盛。”
高强一听果真有报恩寺,心中已知了五分,又问地保:“敢问附近可有住着什么姓杨的人家?”
“衙内却不是神人,怎地一猜即中!”那地保堆着笑脸:“这墙后便是本府押牢节级的下处,那节级便姓杨,叫做杨雄的便是,因他一身的好武艺,又且面色焦黄,人送个绰号叫做‘病关索’。”
病关索杨雄!高强听了这个名字,这一件两尸命案早已了然于胸,便是水浒中的“石秀智杀裴如海”了,石秀被那杨雄的老婆潘巧云诬陷说调戏她而被逼走,心中不忿,夜来守在杨雄家后门外,连杀了淫僧裴如海和帮忙把风的头陀道人,剥下衣裳是为了给杨雄去看,以作洗清自己的凭证。
这件事石秀手段狠辣,心思缜密,两个大活人就这么被他无声无息地了帐,衙门的官差竟是半点头绪也找不到,只能糊涂办个相互斗杀而死结案。这件事虽说是石秀下手太狠,不过他从一个流落江湖、卖柴为生的汉子,到救了杨雄、开了一间肉铺,已经脱离了社会底层,堂堂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却因为这一件奸情而身遭不白之冤,失去了年来辛苦奋斗的一切,也怪不得他心头杀气升腾了。
只是据施大爷的笔墨,这件事却是发生在河北蓟州,与大名府差了一千多里地,地点有所不符。不过现如今那蓟州乃是辽国治下,燕云十六州之一,想必是施大爷YY时不够严谨,考据不细致,摆了这么大一个乌龙,嘿嘿。
回头再看那毛孔目和木孔目犹在争执不下,梁中书耐着性子听着,头已经大了一圈,高强忽然好笑,心中想起一句话来:真相只有一个,而唯一看穿这真相的,就只有一个外表看似常人,内心却是来自九百年后的青年!
正自有些得意,燕青不知何时已来到身前,淡淡道:“衙内面有得色,想必是于这一件凶案已有所得了?”
高强一怔,看到燕青当面,不由想起这位小乙哥是刚因为一件奸情而到了自己手下,眼前却又是一桩奸情了,却不知这大宋青天之下,奸情怎地如此之多哉?
忽地省起一事,忙问燕青:“小乙哥,敢问这大名府左近可有座翠屏山么?”
燕青微微一楞,答道:“是有翠屏山一座,就在本府东门外二十里处,向来人迹不至,乃是荒山一座。——衙内却怎地知道?”
高强心中发急,眼看又是一桩命案就在眼前,那石秀杀了淫僧,次日便通同杨雄,赚了潘巧云和迎儿上翠屏山,问明奸情始末,杨雄亲自下手,将潘巧云和迎儿尽数杀死,发妻的心肝五脏七件事都被掏出来。虽说那潘巧云不守妇道红杏出墙,勾引的还是个出家人,情节之恶劣与卢员外的贾氏娘子不可同日而语,但再怎么说,妇人通奸罪不致死,两条好汉为了泄一时之气,平白将大好前途抛弃了去落草,岂不是可惜?
尤其是“拼命三郎”石秀,可谓是智勇兼备,明断果决的人才,大名府单身劫法场一役,尽显其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若不是出身贫寒不得读书,此人当可与燕青争一日之短长,如能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