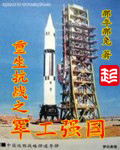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于康熙末年-第2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鼎算计自己,这并不是第一次,望凤庄为一,“茶童子”为二,今日这是第三遭。纵然是泥人,还有三分火气,曹颙如何能一忍再忍?
李家李煦见老,李鼐是个老实人,若是除了这个多事的李鼎,保不齐抄家之祸也是免得掉的。这样想着,曹颙的脸上就多了几分杀机。
李鼎是不能再留了,曹颙心中叹了口气,实没有多余的心思来应付他。
“走,怎么也得去同主人告个别!”曹颙站了起来,有些倦怠。
谁的性命都不低贱,但是若威胁自己的性命,那这恶人也只能做了。自己,委实是个伪君子啊,他在心中自嘲着。
这想起君子,想起堂姐夫孙珏来,对魏黑道:“孙珏就在我隔壁吧,咱们去看看!”
房门掩着,一推便开了,入目尽是不堪。
曹颙转过头,退到门外,心里腻歪的不行。但是想起还要看在曹颍与两个孩子的面上,便对任叔勇道:“刚看到地上有清水了,浇醒他,让他自己个儿拿主意!”
枝仙、叶仙察觉出有动静,往门口看来,见大门敞开,都讶然出声。两人也不是无耻之人。只是信了李鼎的恐吓之词,怕被卖到窑子里,才勉强应承。
孙珏迷迷糊糊的,只觉得怀里空了,还伸手划拉着,口中含糊着叫道:“香彤……”
就听,“哗啦”一声,一盆清水浇到孙珏身上正着。
孙珏被冷水激得,立时清醒过来,他摸了把脸上的水,坐了起来,满脑子的怒气。
屋子里哪儿还有别人?只有两个坐在床上,被溅开的冷水弄湿了衣裳的两个美婢……
因魏黑方才去了李鼎卧房,因此大家轻车熟路的前往。
李鼎喝了酒,今日又如愿设计了曹颙,心里正得意得紧,只觉得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道。
香彤弓着腰身,被弄得气喘吁吁,不停求饶:“爷……爷……彤儿受不得了……求爷怜惜……”
李鼎听了,心里熨帖,却是动得越发厉害,嘴里道:“素日你不是最爱爷使劲的么,怎么承恩不了了……”
“啊……嗯……啊……”香彤嘴里乱叫着,哪里还顾得上回李鼎的话?
李鼎只觉得身下一紧,已是泄了。
两人一起倒在床上,他趴在香彤的肚皮上,动也不想动。
香彤亦阖着眼睛,半晌问道:“爷这是跟哪个狐媚子学的?可折腾死彤儿了!”
李鼎在她的胸脯上揉了两把,道:“舒坦不舒坦,别告诉爷,你不爱这个。”
香彤“咯咯”笑着,往李鼎怀里钻,道:“爷真坏,惯坏戏弄彤儿!”说到这里,也带了几分委屈,道:“彤儿可是想着要同爷白头偕老的,爷可不能厌了彤儿!往后别说是阿猫阿狗,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彤儿也不往前院去!”
因想起刚才被叫出去劝酒之事,她心中也带着几分害怕。自家这位爷,可是个喜新厌旧的主儿,自己到他身边大半年,已经不如先前受宠。
曹颙相貌清俊,孙珏也是仪表堂堂,李鼎见香彤这般贬低两个,心里甚是欢喜,瞅着她比平日越发爱,亲了一口道:“嗯,真是爷的好彤儿,往后等奶奶进门了,爷就抬举你做姨奶奶!”
这话却不是第一次说了,香彤心里虽不信,面上仍带着几分感激、几分欢喜来,娇声道:“就晓得爷疼彤儿!”
远远的传来更夫的打更声,李鼎想想客房的两人,不由笑道:“也不晓得那两位入巷没有?爷倒是要看看,明早这两位‘君子’有何脸面在爷面前作态!”
瞧着那枝仙、叶仙两个像是明白的,香彤还不担心,但是杏儿才十四,又是未经人事的。若是曹颙动手还好,不过见他醉成烂泥似的,也不像能驰骋的。
因着杏儿,香彤想到自己个儿身上。前两年她被老爷开苞时,比杏儿还小呢。就是老爷连哄带吓的,她也是唬得小猫一样,更不要说自己主动去往老爷身边凑。
这世道,做女人不易,做婢子更是难熬。
香彤想起李鼎上床前算计得狠毒,不由婉转求情道:“爷,就算明早曹爷不认,也可使人送到曹府去,听说那位郡主夫人是极贤惠的!爷只是思量着坏了他的名声,这样一个大活人在曹府搁着,不是越发合爷的心么?”
李鼎轻笑一声,道:“傻丫头,你不晓得,有时候这死人比活人越发会说话呢!他若是认账,还好说,不过是多个风流的罪名,碍碍淳王府那边的眼。”说到这里,声音里添了几分阴冷:“他有什么本事,依仗的不过是王府的威风!爷忘不了他给爷的羞辱,这笔帐,总有一日要算回来!只是父亲的意思,如今要借他的力,还要留着他。逼奸至死,就算我们做亲戚的帮着‘遮掩遮掩’,也终究会有风声传出去。到时候死无对证,爷倒是要瞧瞧这位至善君子如何翻身?不过是小人罢了,惯会装模作态,实是令人恶心!”
屋子外的魏黑等人,听得已经是怒气横生,恨不得立时提刀进去,将李鼎剁吧了,却被曹颙给止住。
李鼎这话中,有一句说得不假,那就是他曹颙虽带着至善君子的面子,但骨子里也只是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他已经对李鼎动了杀机,心里拿定主意要灭了这个隐患,但是仍随着魏黑等人过来,为的就是要亲口听听李鼎的恶言。心,平静了,再无愧疚与不安。
一死百了,还折腾什么?曹颙甚感无趣,悄悄退了出去。魏黑与任叔勇、任季勇两个不好妄动,也跟着曹颙身后出去。
回到前院,曹颙带着魏黑与任家兄弟直接寻了小满。
虽然夜深了,但小满心里也惦记着曹颙,正在那里同管家套话,想要往客房这边来。管家被他磨叽得不行,但是晓得他是表少爷的心腹小厮,也不好太过无礼,只好哼哼哈哈的应付着。
见曹颙出来,小满甚是欢喜。忙迎过来:“大爷,您这是醒酒了?小的还担心您醉酒伤身!”
曹颙笑着点点头,道:“嗯,我醒酒了,咱们这就回府去!”
那管家晓得自己主子留客,见表少爷这般出来。主子也没送出来,还以为那边也喝醉,对曹颙道:“表少爷,要不奴才去使人跟二爷说一声,这般实在是失礼!”
曹颙摆摆手,道:“夜深了,大管家就不必折腾表哥了!我府里有事,这就先回去,改日再来造访!”
说话间,众人已经出了大门,却只有曹颙与小满的马。
那管家这才反应出有些不对,这魏黑几个长随明明已经被主子打发回曹家了,这是什么功夫又回来的?门房怎么没禀,自己怎么不知?
到了胡同口,张义与赵同已经牵了马在这里候着,魏黑他们三个的马也牵来。
见曹颙到了,两人忙牵马上前。“大爷,您可出来了!”张义松了口气,话音里尽是欢喜。
“大爷!”赵同虽话不多,但是音声也微微发抖。
月到中天,昏暗中,曹颙看着身边的几个人影,只觉得心里不再那样寒,暖暖的使人心里发酸。
他翻身上马,笑着对众人道:“走,咱们回府!”
众人亦是心情大好,吆喝着跟上,过了半趟街,小满才反应过味儿来,诧异的问道:“魏爷,你们是啥时候来的……”
梧桐苑中,初瑜躺在炕上,却是有些睡不着。
除了出门子,两人成亲这些年来,额驸鲜少外宿。如今在李家歇来,想来是醉得厉害,这醒酒汤可是有人会记得?
那边府里没有长辈,只有位比额驸大不了几岁的表哥。男人家粗心,哪里是会照顾人的?初瑜长吁短叹,实是睡不着觉,不由的再坐起身来。
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暗暗向菩萨祈祷,让自己挣点气,多多的为丈夫繁衍子嗣。额驸如今背着“惧内”的名声,不还是因怜惜她的缘故。她能为丈夫做的,也唯有这个了。
如今,府里的孩子多,也着实热闹。月末,妞妞就两生日了。左住与左成兄弟两个,再过一个月,就要满周岁。恒生将两个月,到冬月末也满百日。
孩子们的好日子不算,这给李家的贺礼也要预备下了。毕竟是李氏的侄子,曹颙与初瑜作为小的,不好怠慢……
初瑜正想着,就听到外间有动静。她唬了一跳,因曹颙不习惯留丫鬟在上房值夜,所以晚上也没有留人。
照看恒生的奶子与乌恩都在东边的暖阁安置,西间里外两间屋子,只有初瑜一人。
她有些怕,莫不是进了贼?
就听是吁了口气的声音,而后是“窸窸窣窣”的脱衣服声。
初瑜很是诧异,低声道:“额驸?”
不是曹颙,是哪个?他怕扰了初瑜,没有进里屋,想着在外间对付一宿得了。
听初瑜吱声,曹颙也颇感意外,道:“这都多晚了,你咋还不睡?”
初瑜已经下炕来,摸到地上桌子边,点了灯。
曹颙挑了门帘进里屋,见初瑜只穿着中衣,忙道:“快回炕上躺着,仔细见了风!”
初瑜见曹颙浑身酒气,甚是担心,道:“额驸,使人往厨房弄醒酒汤吧,要不明儿头疼!”
曹颙往炕上一躺,摆摆手道:“明早儿再说吧,这都四更天了!”
初瑜俯下身来,帮曹颙去了靴子。
曹颙因酒后见风,现下头已经开始疼了,拉了初瑜上炕,道:“你帮我揉揉!”
初瑜见他手心冰冷,额头又有些热,忙道:“额驸着凉了,还是使人往厨下熬碗姜汤,发发汗吧!”
曹颙在李宅时虽没醉,但是经过夜风这一吹,身上也有些发热。初瑜的小手软乎乎的在曹颙身上这一摩挲,他便有些个意动。
今晚,见识了活春宫,他也不过是个寻常男子罢了,这心里也憋着欲望呢。
听了初瑜的话,他翻身将初瑜压到身下,在她的脖颈中闻了又闻。这淡淡的香味儿,比那些呛人的脂粉味儿好闻得多。
初瑜低声道:“额驸……”
“老婆,不用姜汤,也有发汗的法子……”曹颙只觉得自己的声音分外邪恶,像是哄骗小女孩的怪叔叔。
“老婆?”初瑜头一遭听他这般称呼,心里带着几分好奇,嘴里问道:“不用姜汤,怎么发……”
后半截话,她却是说不出了。
就见帐幔“簌簌”的动个不停,屋子里传出喘息声……
第347章 吊唁(上)
十月初七,圣谕,太仆寺卿曹颙“居官尚勤”、“实心理事”,恢复原品;升大理寺卿兼管太常寺卿事荆山为礼部右侍郎,仍兼太常寺卿;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徵璧,为工部右侍郎。
虽然伊都立嚷着要凑份子吃酒,贺喜曹颙官升从三品,但是曹颙还是婉拒了。不过,大家也不恼,因为曹颙说了,明日请众人到前门最大的馆子吃酒,他做东。
今日他不得空,因是故辅国公鄂飞的头七。
曹颙早就同初瑜提过,要带她同去辅国公府吊唁。礼金与香烛、祭幛早已经准备好的。
因这时的丧仪,“非至亲者,不着缟素”,曹颙虽在鄂飞临终前叫了声“义父”,但是也不会巴巴的穿了孝衣过去张扬。
如今,鄂齐的袭爵旨意尚未下来,公府的家产还未收拢,跑出个“义弟”来吊唁,这算什么事?
曹颙将帽子上的缨络去了,换了石青色长褂;初瑜梳着两把头,去了首饰,也穿了石青色长褂。夫妻两个,乘坐一辆青呢马车往方家胡同去。
鄂飞前些年虽然挂着内大臣,这两年却是没兼差事,加上他本不是交友甚广之人,因此来吊唁的外客不多。多是一些与公府有亲的低品级的黄带子宗室,还有就是侍卫处那边的人。
大门已经糊了白纸,白门挂着鼓。曹颙与初瑜两人下车,就有国公府这边的管事迎过来。
曹颙把名帖递上,同初瑜一道,跟着那管事,进了大门灵棚。
就听那管事扬声道:“太仆寺卿曹老爷携妻和瑞郡主到!”
男客在灵前祭奠,女客则被迎到灵后。
因讲究“死者为大”,来客除了长辈不跪外,平辈与晚辈都要跪奠。
灵棚里搭了月台,灵柩摆放在上,灵前拜垫上铺着红毡子。若是来客与逝者平辈或者只是寻常交情,则在红毡子上跪奠。
红毡子下是白色跪垫,若是晚辈或者是至今好友,则去了红毡子,在这上跪奠。
想起鄂飞孤苦一生,曹颙上了月台,走到灵前后,撩开了红毡子,跪在白垫上,很是恭敬的三奠三叩。
每一奠都是有两个家仆送上奠酒,曹颙接过斟满酒的奠爵,双手举过头顶,洒入奠池少许,随后将奠爵递还给家仆,随即叩首。
旁边除了鄂齐带着几个堂弟堂侄跪在灵左还礼后,还有以唢呐、堂鼓、九音锣组成的官鼓大乐。
随着曹颙一奠一叩,就是一棒大锣,甚是庄重肃穆。
初瑜到了灵后,本家孝妇带着女眷跪在灵后右侧哭丧。
初瑜行的礼与曹颙不同,是旗人女眷的“摸头礼”。她由喜云、喜彩两个扶着,走到灵后拜垫前,双腿一屈,坐在脚上,头上由前方微微一顿,用右手指摩挲下两把头的右翅,就算是礼成。
叩奠完毕,才是上前举哀,初瑜从右侧进入灵帷幔帐里,用手中的帕子捂住脸,哭了两声。
同其他宾客不同,初瑜的哭却是真哭。因曹颙已说了认义父之事,还道鄂飞之前对他多有照拂。如今,老人家孤零零的走了,身后没有亲生儿女哭丧,只有一嗣子,怪可怜的。
已经有执事上前喊道:“请节哀少痛吧您哪!”
待初瑜到月台下的桌子边,有内眷举着铜茶盘,里面是白布包头及白蝠,口称:“请您给亡人免免罪吧!”
初瑜伸手接过,戴在头上,面带着哀容落座。
有几个国公夫人、将军夫人,听说初瑜是郡主格格,上前俯身见礼,寒暄叙谈。自然,不宜喧哗说笑,大家都是压低了音量。
女人多了,话里话外,难免说起各大王府贝勒府的轶事来。
其中,有位镇国公夫人看着很是富态,听说是简亲王府的近支,低声对众人道:“我们王府的那位福晋,向来好强,在我们这些妯娌面前,从来都是眼睛望到天上去。好强又如何,没有哪个好命,也强不到哪儿去!”
有位将军夫人,看来也是晓得些简亲王府典故的,好奇的问道:“婶子说的是哪位福晋,侄儿媳妇瞧着那位伊尔根觉罗福晋倒像个明白人。”
镇国公夫人咂咂嘴,摇摇头道:“明白人又能如何?虽生了三个阿哥,只占住了一个,身子骨也不甚结实。大福晋虽没了,却留了两个嫡出的阿哥在。前年进门子的,又是个有脾气的,她如今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将军夫人却是有些糊涂了,道:“婶子说的,可是那位伯爵府出来的继福晋?”
镇国公夫人道:“自然是她了,前两日小产,滑了个成型的男胎,都五个月了,亲家太太赶过来,哭得昏厥过去!”
“啧啧!”那将军夫人亦感叹道:“五个月,那可伤身子!这位福晋侄儿媳妇也听说过,若不是因孝期逾岁,耽搁了年纪,就是皇子阿哥也配得。”
镇国公夫人道:“不过是命罢了,我们王爷……我们王爷那个兴致,你也晓得……对内眷不上心呢!这些年来,王府里没了的孩子还少了?别说这没出娘肚子的,就是当年的大阿哥与二阿哥,十来岁了,不还是说没就没了?如今伯爵府那边也不如过去风光,他大哥因不孝被驱逐宗族,还有个哥哥虽然当差,也不过是个小官。如今这福晋端着个架子,也不晓得给谁看呢!”说到最后,话里却带了几分幸灾乐祸。
初瑜在旁听着皱眉。低声问道:“敢问两位,说得可是简亲王府的完颜福晋?”
镇国公夫人点点头,道:“可不就是说她!这做女人,不能太钢性了,还是应惜福才好!”
初瑜心中叹了口气,不胜唏嘘。虽然没有见过完颜永佳,但是她却是早就听宝雅说过的。晓得她是永庆的胞妹,出阁前是宝雅的闺中密友。
听宝雅话里话外,对完颜永佳甚为推崇,初瑜便晓得她不是寻常女子。宝雅还无意提过,完颜永佳在曹府养病和当初大家一道去小汤山庄子游玩的情形。就是曹颂,也不止一次的提过这位完颜姐姐。
不知为何,想到那位嫁到简亲王府为继福晋的完颜小姐,初瑜的心中总是怪怪的,好像自己“鸠占鹊巢”了一般。
她还曾经思量着,若是自己没有被皇玛法指婚给额驸,情况又是如何?
凭着完颜永庆与额驸的交情,还有完颜小姐不用选秀这条,两家说不定已经有了联姻的打算。
初瑜不晓得自己猜对了几分,只是过去的已经过去,她也不会在曹颙面前多言探究。
直至今日,听到完颜永佳的不幸,初瑜才省得,自己是介怀的。虽说旗人儿女不像汉家那样防范过甚,但是少年男女往来也是不便宜。若不是至亲,或者两家父母有意将孩子送做堆的,大家鲜少有机会接触。
在江南,同曹颜、曹颐相交,见过少年曹颙的是完颜永佳;在京城,与曹家兄妹往来交好,愉快交游的,是完颜永佳。
就是同额驸说起过去的事,偶尔出现的女子名字,亦是完颜永佳。初瑜原还没觉得什么,这些年渐大了,想得也多些。
不管当年真相如何,毕竟已时过境迁。初瑜喟叹一声,如今她能做的,就是为那位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完颜小姐祈祷早日康健。
曹颙在灵前叩奠后,在月台阶下,接了知宾用铜茶盘双手高举的孝带,在腰间系了,这叫“穿小孝”,算是对逝者的恭敬。
还没坐下,曹颙就看到两个熟人,领侍卫内大臣兼掌銮仪卫内大臣阿灵阿与銮仪使三等辅国将军讷音图。因鄂齐也在掌銮仪卫兼着銮仪使的差事,所以这两位是上官与同僚,今日来得都比较早。
阿灵阿看到曹颙,冲他挥了挥手,道:“曹额驸,来这边坐!”
这论起品级,阿灵阿是超品公,曹颙只是等同一品武官;说起辈分来,阿灵阿贵为皇后之弟,是七阿哥的舅父辈,曹颙则已经是孙子辈儿。
虽然晓得他是倒霉的八爷党,但曹颙避不开,还是应声过去请安。
曹颙任太仆寺卿这大半年,同銮仪卫那边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讷音图,两人也算是混熟。
见曹颙过来,讷音图很是亲近,指了指身边的椅子,请他坐了。
方才曹颙上月台上叩奠时,阿灵阿便瞧见他,见他面露哀思,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