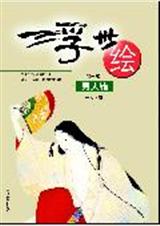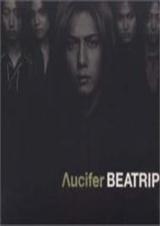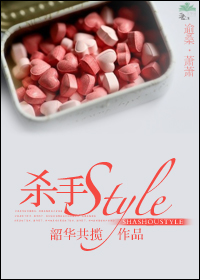恶质男人-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来敲门说要收碗筷,我匆匆去开了门,拿了她新端来的冰汽水往嘴里一倒,提醒她临走前记得将房门反锁后,就往浴室走去,我松开水龙头淋浴,浴毕己不觉得发热,头却开始晕起来了,我摸着墙走出来,出乎意外地闻到一服香水味,我知道‘她’在房里,很快地便往床上瞧,她就躺在那里,穿了一件红衬衫和黑迷你裙。”
“她不再像我十二岁时那么纤瘦,扣子几乎全敞开着,也没穿任何内衣,两腿还故意拱起,让我窥见她的私处,而她看看我的眼神,像是要一层一层把我剥开似地,她说:”五年了,我终于等到你长大了,让我好好爱你。“我听了头开始发晕,想作呕,不得不冲到浴窒去躲避,下体却胀到发痛,我知道自己必须自行解决,于是对着马桶开始自慰起来,不想她跟了进来,我心里起了毛骨悚然的感觉。她要碰我,我用力一挥把她推开,她倒在地板上,我不想看她的模样,只忙着抚弄自己的身体,本以为一次就够了,不想停了两秒又发热起来,我只好继续,但却同时困得想倒在地上,到第三次时我终于害怕得掉下了泪,我以为她终究要抓到我了,没想
到她却躺在地上兴奋地抽搐起来。“我见她一副昏死的模佯,逮到机会,抽腿就跑出卧室,
我不知道该躲在哪里,突然想起齐芳,便去敲她的门,我看到一脸纯真的她,就像见到天使似地放心了。她问我,“是不是作了恶梦?”,我说:“是,很恐怖的那一种。”,她也告诉我,她作了恶梦,身体流了血,并要我去看她的床单,真的是有一摊血印在上面、我知道那是课本上所讲的初潮,但是我好困,往她的被里一钻,答应等睡醒以后一定告诉她。但是等我再次醒来时,整个世界都变了。“他闭上了眼睛,激动的说:”请相信我,我没有主动碰那个女人,更没有碰我妹妹。但没有一个大人肯相信我,最后连我最信任的妹妹都被他们教到回头反咬我,“那绫搂着他,为他拭去额上的汗,细语不断地跟他保证,”我相信你。“然后回头找寻母亲的身影。想征询下一个步骤,没想到除了躺在矮桌上的笔记本外,己不见母亲的踪影。
那琬琬留下一张便条——小乖,我去齐放的公寓等外公。没把他摆平以前,你们不要跑回来。至于把齐放从浅度催眠里唤醒的方法很简单。就服我们事前约定的方法做,先吻他,然后跟他讲‘那一句’,他自然会醒来。但是如果你想来机占他便宜的话,那尽管继续问下去,何不问他,“你这一生中,最爱哪一个女人?”但我要警告你。受到催眠的人是有意识的,他也许无法拒绝你的问题,但被叫醒后,可是字字都记得一清二楚。祝好运!
那绫是想知道他最爱哪一个女人,但不愿这样“欺负”
他,便循规蹈矩地照母亲的指示在他唇上印下一吻,轻道一句,“沉睡的小王子该醒来了。”
齐放听到这句话后,眠咒解除,慢慢睁开眼,呆了一分钟才回到现状,意识到自己说过的话,他茫无头绪地将脸埋入她的手掌里,呐喊,“天啊,我对你说了什么教你要看轻我了”
他是这么地在乎她的看法,那一对认真深邃的眼眸和那个在“重庆森林”里洒脱酷炫、轻狂不定的Ray是多么的不同。他爱她!不用他亲口说,她知道他爱她。
那绫眼里涌出热泪,边啼边笑地坐到他身边,给他一个的吻,单指滑过他性感十足的喉结,哑着声音说:“不,正好相反,我只会愈来愈看重你。”
“是吗?”他怀疑地盯着她的唇问:“你妈人呢?”
“去等外公了。”
“现在可不可以吻你呢?”不等她的答案,他的两手已开始拉下她洋装后面的拉链。
“我觉得……”那绫软泥似地应了一句,“现在再适合不过了。”
齐放眼里充满爱火,紧盯着那绫性感有致的身子瞧,接着低头将下巴顶在她饱满浑圆的酥胸间摩挲着,两手则沿着她的背脊将她拉近自己。他的唇每在她身上挪动一寸,他就会喃喃地对着那一寸的肌肤说话。
“我爱你,爱你的人,更爱你的心,我很高兴你那天在街上把我这只摇尾乞怜的狗、沙猪,甚至欠扁的企鹅‘捡’回家,更抱歉自己在事后不知好歹地躲了你一个月。我还要感谢你、感谢你努力不懈地打电话给我,把我缠到疯,疯到不得不认识你,最后陷入非爱你不可的地步。”
那绫没有被他的甜言蜜语冲昏头。反而将他往沙发上一推,首次拒绝他主动的亲热,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你知不知道每次让你骗到,我就浑身不由自主地发烧,甚至战栗起来!”
“这有什么不对?这表示我们对彼此有反应,是天生一对。”
他忍不住伸手要摸她,却被那绫打掉了。他甩了一下发痛的手,一改酷酷不在乎的模样,妥协
说:“秀色可餐小姐,你别凶,你……”
“你可不可以给我闭上鸟嘴,就这么一次别来碰我!”
“你怎么突然变了?”他转过头去,不愿正视她。“莫非你听了我的故事,开始看不起我……”
“不,不准你往那头歪想。”那绫双手大挥了几下,把他的脸转正。“我要你收敛魅功是要你戒掉以攻为守的坏习惯。同时也请你不要把我看成那些只当你是种马、只顾着贪恋利用你的身体,却不在乎你心里的感受的女人。”
“所以?”他眼不挪地质问她。
“所以你得接受我只是一个凑巧无条件爱上你的女人,而非在床上反咬你的”猎物“。
“然后呢?”
“然后接受我偶尔也想好好爱你,乐于取悦你的事实。”
他目光转厉,咄咄逼人地问:“你刚才说无条件的爱上我,是无条件到什么程度?”
“无条件到即使你这只蟾蜍变不回王子的模样,我也照缠你不误。”
“包括我是个穷光蛋,不再是个富翁之子?”
那绫点头。“有一技在身的人永远不算穷。”
“听你的口气,你似乎愿意跟我一辈子了?”
那绫瞠目望他一眼。“你这是在问真的,还是问假的?”
“当然是问真的。”他摆着一张招牌酷脸,问:“喂,女人,怕不怕跟我一辈子?
他这哪算得上求婚!口气霸道得跟土匪无异。
那绫知道那是因为他的流浪狗情绪又作祟了,而要让流浪狗服帖的最佳办法是让他尝到安全感。于是,那绫把自己当成一根“爱的骨头”塞躺进他的怀里,柔媚多娇地看着他,“当然不怕,因为我已准备好要缠你一辈子。”
于是,她轻手轻脚地缠上他,并且警告他举在半空中的手,“你别动手哦,动手的话,你就完蛋了。赶快把手放到你的颈子后压着。”
齐放照办,但还是忍不住抗议,“面对秀色可餐的佳肴,不动刀动叉是很难的事。”
“有人伺候喂食你还嫌,再嫌的话,我不跟你玩了。”齐放总算会意了,他咧着嘴一脸笑,将四肢往外一摊,摆成一个“大”字型,慷慨就义地对她说:“既然如此,全凭娘子您处置了。但先让我再告诉你几件重要的事。”他说着又直起上半身,继续道:“我想,我已比昨日更爱你一些,却又铁定不及明天来得多,而这种感觉会与日俱增会愈来愈严重。”
“很好。因为我也是觉得自己比前一秒更爱你一点,却又绝对不及下一秒来得深,而这种感觉分秒必‘增’,愈来愈沉重。”
“换言之,你真的爱我?”
“我真的爱你。”
“没骗人?”
“骗你是海狗。”
他开始学海狗的叫声,然后呻吟地问:“海狗怎么叫床的?”
“不知道,你要去问母海狗!”
“等等,你知道雄抹香鲸的性器有多长吗?”
“我又不是雌鲸,怎么会知道?”
“你想知道吗?”
“不想。”
他假装没有听到。“太棒了,最短的起码有三公尺那么长。”
“你瞎说吧?”
“谁瞎说,我以前的一个女朋友是海洋生物学家。”
那绫不答腔。他再度开口,“你知道雄狮要交配几次才会让母狮受孕”莫非齐先生你曾经又有女朋友是动物学家?“
“没那么高档,只是兽医而已。”
那绫听到这里,轻唤他一声,“齐放。”
“嗯?”他的声音难得紧张地抖着。
那绫没想到他这个大情圣也会有紧张的时候。只好抱着他硬邦邦的肩头,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一个女人主动爱你并不等于上钉床好吗?请你放轻松。”
“既然你这么坚持,我这回真的全凭你处置了。”他躺回椅上,十指互相交握在胸前,一副让牙医摆布的模样。那绫后来发现,要驯服他接受自己、不仅要具备孟母三迁的耐性,更要有亚马逊女战士的勇气。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她没料到,他这只炫酷不祥的丛林黑豹竟也有如绵羊低头服膺人的时候。
凭着这一点,她更爱他了。
第十章
那琬琬踏出假期饭店,乘着都市风,足踩轻忽不定的碎屑与落叶,安步当车地往齐放的公寓大厦走来,远远地,她注意到一个深具魅力的中年绅士,坐在石阶前读报,精工裁制的深色裤管下露出两截银灰色的长棉袜,换作他人看来会很滑稽,但他特殊的银色头发却降低了可笑度,让她体会到流行与风尚的戒条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她踏上阶梯,马上发现他的报纸是读假的,因为他从一百步外就盯住她,甚至当她拾阶走近他时,那双紧迫盯人的琥珀色眼眸连瞬也不会瞬过。那琬琬打算快速跳上阶,不理这个男人。不想他突然开口问一句,“好心的女士,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真爱是什么?”
嗓门大刺刺地吓人,害她差点踩空。那琬琬弯身拔下自己的高跟鞋按摩脚板后,问他,“你在问我吗?”
“当然是。”他从容不过地回答,两眼盯着她纤细的脚踝。
那琬琬睨他,穿好鞋子后才说:“我没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吧!”
“如果你肯告诉我,我会付你一万块。”
那琬琬知道纽约的疯子比巴黎多一倍,迟疑地,她是遇到疯子了,于是试探地说:“如果你肯付我十万块,我就告诉你。”
对方连眼皮郡不眨,嘴角泛起一道世故的笑痕,从衣袋里掏出一本支票簿,约下开出一张十万美金的即期支票给她。
哈!还是个有钱的疯子!那琬琬接下支票,不是因为贪财,而是想确定他是不是在寻她开心。
“钱在这里,请你告诉我答案吧。”
那琬琬在高他一阶的石阶上落坐,把支票退还回去,顺便给他解答。“真正的爱,是无价宝,财富买不到,权势占有不了。”
“是吗?”他笑笑地收回支票,继续问:“你可不可心再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让一个女人真心爱我?”
“你的爱藏在心底不肯付出,就不是真爱;同时,你若没有接受,付出的爱必将枯竭。”
男人将报纸搁好,回首仰望她,眼底有欣悦,“我从来就不相信一个美丽的女人会是聪明的。”然后贸然地将她打量一圈,慢条斯理地补上一句,“但是今天,我碰到一个例外。”
那琬琬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为他感到可怜。“多悲哀你错过了多少个好女人。”
他楞住了,久久才附和,“是该悲哀没错。我有一个漂亮得像芭比娃娃的太太,但我却不爱她。”
“哦,你不爱你太大?”那琬琬不怎么感兴趣地问。
“她也不爱我。当初碰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之中一个贪财,另一个好色、各取所需。”
那琬琬听了点一下头。
他继续对她倒垃圾,“她最近碰上一个年轻小伙子。跟我闹离婚,但我不答应。”
“我们家乡有一句古谚,天涯何处无芳草。”那琬琬扫了他一圈,忍不住多嘴一句,“你既然不爱你夫人,为什么还硬要绑着她?”
男人好笑地看着她,“当然是为了钱啊!你不知道在这里养个下堂妻是多昂贵的一件事,投资报酬率不到千分之一。”
他刚才还大方地要送她这个陌生人十万块哩,现在反而变小气了。那琬琬瞄了他一眼,“你确定不是因为嫉妒?”
“我又不爱她,为什么要嫉妒?”他好笑地反问她。
“嫉妒她比你先找到爱情,你却一个人孤零零的过日了。”
他看着她,原本和蔼的脸色变得索然无味,语调也放淡了。“听我一句话,美丽的女人最好还是不要太聪明,因为会破坏男人的想象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独自安静地看份报纸。”他下完逐客令还从口袋里掏出支票,递给她,“这是十万元的酬劳,请收下。”
那琬琬也不动气,知道自己搔中他的痒处,照他的要求收下他的支票,起身扭着高跟鞋往公寓的会客大厅走去。
当她看见由侄儿相伴的老父拄着一根拐杖,严肃地稳坐在中庭的沙发椅上时,胃忍不住打结。她能想象父亲见到她,除了讶异五秒钟外,一定会出言责难她活了快半百了,竟然连归宿都找不到。那琬琬内疚二十多年来没为女儿尽过心力,就这么一回,她不能再躲避父亲的权威,于是从皮包里取出录音设备,毅然走向父亲。
她先发制人,“爸,这里是公众场合,我们上楼后再谈。”
“阿绫人呢?”那元鸿跟在女儿身后,冷冷地问。
“在我住的饭店里,很安全。”
“只要跟你扯上边,哪里都不安全。”跟女儿久久不见,那元鸿仍是固执地不给女儿好脸色看,随女儿上电梯后,询问一句,“你还是不打算找个男人嫁吗?”
“爸,拜托,别跟找提这个。”那琬琬停在齐放的公寓前找钥匙,想起自己竟粗心地将钥匙遗忘在笔记本里,她懊恼地回身要道歉,没想到一个银发洋人头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自父亲和侄儿的身后冒出,害她差点叫出声。
那个洋人脸上挂着魅力十足的笑,说:“亲爱的,不是提醒过你,我的公寓在顶楼吗?你怎么听听就忘了?”
他说的还是中文呢!虽然谈不上字正腔圆,但足以让那元鸿回头问:“你是谁啊?中文讲得不错。”
“谢谢。”对方主动伸出于,殷勤地握住那元鸿,自我介绍。“我是拉斐尔?狄米奇尼,齐放的老板,也是”弯弯“的男朋友。你一定奇怪弯弯会看上我,千万别怪她,那是因为我们意大利人都有马可波罗情结,自从跟中国人有缘,碰上后很有亲切感。”
狄米奇尼的拍马屁功是世界一流的,对任何国籍人士都适用。
“真是这样吗?”那元鸿问。
“当然是,没有你们中国人的饺子、面条和烙饼,意大利人也翻不出新花样,早在五百年前就要被饿死了。”说完两手将他们扶进电梯。
那琬琬两眼圆睁地盯着他瞧,不是不信有人撒谎不打草稿,而是不相信他竟夸张到能用中文拟稿。
狄米奇尼瞧见她一脸吃惊的模样,很快地以法语轻声跟她解释,“你忘了钥匙,齐放和那绫打电话给我,请我帮你解围。”
“所以你在大门口时,早就知道我的身分了?”
他笑而不答,表示同意,手朝电梯外摆了摆,请大伙光临他的寒舍。
那琬琬踏进他的豪华寓所后,碍于父亲和懂英文的侄儿在场,不便摆出凶相,只得用法语表达意思,“帮个忙,我的中文名字是”琬琬“,不是”弯弯“,谓你发音正确一点。请问你的厨房在哪里?”
他似乎很欣赏她恼怒的模样,不急着为她指引,先招来仆人伺候客人后,才回身抿嘴忍住笑意,领她入厨房,“抱歉,因为时间紧迫,电话收讯不良,再加上齐放连珠炮似的解释,有些专有名词听不太清楚。”
“谢谢你替我解围,我想我能应付我父亲,请你暂回避一下,最好避到楼下去看你的报纸。”
狄米奇尼不同意,“我想你会需要我。毕竟我认识齐放比你久,又是他的老板,说服力比你强。”
“对不起,这是家务事,我不要外人在场。”那琬琬坚持要他闪人。
狄米奇尼只好打出王牌,“听着,我手上有一封齐放的母亲交给我的信。”
那琬琬楞住了。“你认识齐放的母亲?”
狄米奇尼点头,有心地附加一句,“学生时期是关系清纯的男女朋友。”
那琬琬假装没听到他的解释,将话题转回那封信。“你说你收到她的信,什么样的信?”
“她在信上告诉我,她已订好机位,将带儿子搭机来美国散心,人到纽约会再联络我,但我从没等到她的电话,以为她改变主意了。日后发现信上邮戳显示,她是在失踪前一天寄出的。”
那琬琬听完,思索片到,精神振奋起来,“那就证明她没有跟司机离家出走的意图。”
狄米奇尼完全同意,“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那就真是车祸了。”那琬琬想想又猛觉得不对劲,因为机场在桃园,她却在动身远行的前一天跑到东北角,那里除了带不出国的海产和美景外,应该没有任何事让她非走那一趟死亡之旅不可。直觉地,她脱口而出,“那场意外事故有可能是预谋的。”
狄米奇尼听了整个人僵在那里,“你凭什么这么揣测?”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来龙去脉,我得先应付我父亲。”
“我帮你一起应付。”
“嘿,这事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大事,请你不要随便附和。”那琬琬防贼似地看着他。
狄米奇尼一脸严肃,说:“如果我当年懂事些,齐放该是我儿子。”
那琬琬才不管他后悔莫及的理由是什么,坚持地抗议,“我不要你介入这件事。”
“抱歉,这事也扯上我未来的事业接班人的终身大事,我管定了,且非全程参与不可。”狄米奇尼说完,扭头走了出去。
此后,整个事件就被狄米奇尼所主导。那琬琬除了拿着遥控器,在他可媲美音乐厅似的阳光书房放带子外,能说话的时候不多。狄米奇尼的中文不算差,但因为不是一个打马虎眼的人,只要有半句听不懂,马上就发问。那琬琬觉得他很烦,根本不理他,惹得老父看不过去,不得不接过遥控器塞进孙子手里,自愿担任狄米奇尼的通译,还怪她一句,“都那么大的人了,还不懂得发扬咱们中国女性的美德,狄米奇尼肯要你,真教人百思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