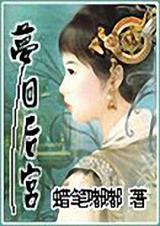(全职高手同人)[喻黄]月半弯-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招衙欢嗑谩ocx存着,还暗搓搓在lo上没打tag放过一段时间。现在,终于,二万五千里,到达了这里……哦并没有完。
G市北京路上的财政厅旧址……棒!特别地,喻文州,感受一下(。
'喻黄'月半弯(八)
我一个双鱼座,为何还在试图说逻辑……(邓布利多摇头。gif
八、鹊灰
有些事一说开了就不可收拾,像开了闸的水,浩浩荡荡地冲出来。
黄少天本就不是擅于遮掩的人,情动溢于言表,一举手一投足都是跳脱和生动。他不似喻文州般心思持重深情款款,唇齿含笑间皆是奔放的热烈。
人不多的时候,黄少天会在并肩时偷偷拿手指刮他的手背,等到他终于熬不住,避开人流用身体半掩着,悄悄握一握他绵软的手心,才冲他扬起脸,满是快意的神情。
自从知晓了彼此的心思,他觉得黄少天笑起来的弧度似乎比以往多了一分,思考时歪着的头似乎也比以往斜了一度,看着他的眼神似乎更比以往热了一成。从前黄少天对他笑,他看着自然是喜欢,却总觉得是在别处的;现在黄少天对他笑,仿佛都是为了自己,不管是不是真的,心里就先暖暖地荡起来。
有段时候北边风声紧,两个人都不得闲,一个多礼拜没有出来见面。他想黄少天约莫是明白他自己忙,喻文州只会更忙,也不再来扰他。直到一个周五的傍晚,他接到黄少天打来财政厅的电话,说请他在惠如楼一道食饭,多晚都务必要来。
放下手头的事情已是九点多,他匆匆赶到惠如楼,走上二层,厨娘端着冒了白汽的蒸笼走进走出。绕过酸枝通花板隔,黄少天约的厢房在最里头一间。
还未到暑气散尽的时候,青铜吊扇有气无力地嗡嗡转着。他推开门,见黄少天伏在桌前,一双手把玩着象牙木筷,桌上早就齐齐摆满了十几样点心。
喻文州看他有气无力,最近报界肯定也是没得安生,累得一张原本红彤彤的脸上添了几分蜡黄色,便走过去坐下,摸了摸他的脑袋,“累了怎么不早点歇着,这么晚了还非得约我出来?”
黄少天只一言不发,手上动作停了,跟着趴了一会儿,突然直起背扯过他的领子。
“我想你了。”嘴唇终于分开的时候,他听见黄少天嗫嚅着说。
他只觉得胸腔里泛过一阵酸涩,再次欺上他的唇。黄少天低低地小声喘着,用力扶住他的肩膀。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满洲窗里外,月圆人圆。
木棉树飘起了叶子,周围的同事一日比一日少,留下的人经常也是一副愁云惨淡的面容。只是广州人好像天生有一颗宽心,早茶粥铺照例生意红火,戏院门口永远排起长队,东堤烟花,陈塘风月里眼波流转,“理他家与国,且看眼儿媚。”
说不清是该叹还是该服。就连叹字,在广州话里一样有享受的意味。
任去者去,留者自留。
中秋刚过不久,喻文州与几个同事在陶陶居食过中饭,去莲香楼买了莲蓉月饼。黄少天爱甜食,又嫌蛋挞蛋糕太腻,莲蓉入口幼滑,莲子清香扑鼻,是他最中意的。
长堤大马路上热闹虽不如以往,周末的日子总还是熙熙攘攘。喻文州提着月饼下了公共汽车,就看见黄少天在明珠影画院边上向他招手。
黄少天个子不高,他却总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眉目间还带着几分少年气的男人小跑几步,迫不及待地来到他面前。
“我把电影票弄丢了。”黄少天开门见山。
喻文州料到他这么殷切一定是有什么事,也不恼,“那请问黄生有什么好去处?”
黄少天拽过他空着的一只手,“你随我来。”
又坐在黄少天的脚踏车后头的时候,喻文州觉得眼前好像还是那个不甚宽阔的十四岁少年的背,脊椎骨贴了洋布料子蜿蜒着往上,手指碰上去,体温就隔着一层温温地满出来。
可毕竟是不一样了。出了闹市区,他犹豫了一下,先前扶着坐垫的一只手往前探了探,圈上细瘦的腰。车龙头晃了几晃,又重新稳住。黄少天口里唧唧呱呱地念叨,“你要扶先说一声啊吓得我……”
喻文州笑了一下,又把脸轻轻靠上他的背。
黄少天不说话了。天上有很低的声音传来,他抬头看看,几个黑点正往南面飞去了。
入秋刚下过一阵时候的雨,白云山间雾霭缭绕。黄少天把脚踏车扔在山脚,拿了车筐里的月饼跟荷兰水,被喻文州伸手接了过去,“你骑了一路,我来吧。”
黄少天抢过一瓶,拧开盖子,荷兰水在车筐里颠过,白色的泡沫欢腾地跳出来,溅了他半身,正手忙脚乱地去擦。喻文州好笑地摸出左边口袋里的手帕,“急什么,渴也没有这样的。”
黄少天咕咚咕咚喝下大半瓶,满足地呼出一口气,对他说了一声“走吧”,就往前跑去。喻文州几步追上,拉住他手臂说,“等一下。”
黄少天闻声回头,刚要问什么,猝不及防地被擒住了唇。
被液体润过的嘴唇鲜艳又饱满,实在太过好看,让人忍不住去亲近。
黄少天顺了气,忽然竖起眉毛问他,“说吧,以前我俩喝粥的时候,饮茶的时候,吃面把面汤全喝干净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这么想过?”
他老实地点头承认,换来一个绽开的笑容和踮起脚尖带着糖精味道的吻。
岭南的树木一年四季常绿,黄少天挑了一条偏僻小路上山,踩着小叶榕盘错的根,扶着油杉粗壮的枝干往上爬,鸟鸣和瀑布声淌进耳朵里。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
黄少天拉着他在一处溪边坐下,拿空了的玻璃瓶去接溪里的水。喻文州等他回了来,掰开一个莲蓉月饼塞到他口里。
他笑吟吟地偏过头,咬住圆弧一边,一半伸在外面,又蹲下来送进喻文州嘴里,这才从中间咬开了。
他本来就是直接的人,喜不喜欢都巴巴地写在脸上。这会儿干脆地往喻文州身上一靠,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古树高高低低,仿佛把世界都隔了。
喻文州摸着他的头发,“真是一方清净地盘。”
黄少天抬头问他,“你出去以后住过南京,北平,武汉,也呆过巴黎,又去过瑞士意大利,比这样的地方应该见过不少吧。”
喻文州便同他天南海北地说起来。南京的梅花,北平的红叶,武昌江水奔腾,枫丹白露的宫殿和密林,阿尔卑斯山脚湖光潋滟,威尼斯的河道响着刚朵拉的摇橹声。
他说得入神,旁边却没了声响。他伸手捏了捏垂在身边的另一只手,“少天?”
黄少天的睫毛抖了一下,抬起黑白分明的眼睛看他,“我听着呢。”
在想什么呢。喻文州看他的眼神似乎没那么专心,刚想问他怎么不说话,只见黄少天翻了个身,凑到他跟前说,“那些地方那么好,可你怎么还是回了广州。”
喻文州不再说下去,迎面把他拥进怀里。
回到城区的时候,气氛有些不寻常,连天边的夕阳也红得不同以往,血染似的触目惊心。
车子拐弯上了北京路,远远地就听到哭嚎。有人往江边的方向跑,也有人一身脏污地跑回来。
喻文州扯扯他的衣襟,“少天,别过去,从惠福东路拐回家。”
人越来越多,黄少天下了车推着,却还是往前去,小心地握了握他的手,“没事,我想过去瞧瞧。”
长堤大马路上堆满了瓦砾,还有砖块和沙子在不停地往下掉。骑楼下面的惨状让人根本不敢看,远处的楼房还在燃着。
行人摇着头念,话语里带着哭音,“本来这附近就没有防空洞,从前都只好往爱群大厦这样的楼里避。今日想躲去永安堂,结果门反锁着,只好挤到骑楼下面……”
一片触目惊心里他看清了砸在焦土上的匾额:明珠影画院。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克砝码,也足以让天平倾斜。
黄少天敲开喻文州家门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深秋的月色都是冷淡的,白得像冰。
喻文州问他,你冷不冷。
刚刚在郑轩那里喝了粥,还挺暖。他答道。
最后他掏出纸钞要付钱,说我白吃你那么多次,这次就多付一点吧,不用找了,也不知还能不能有下次。
郑轩把十块钱摔在地上,说黄少天叼你老味,我虽然懒……
他话还没说完,两个人都笑成一团。
黄少天说于锋跟部队去了云南没人给你送鱼了你可千万别卖了你这艇,我还想回来喝你的粥。郑轩说好,不要忘了你也是去打仗,自己多小心。
郑轩做的粥,料都比别个的多一倍,你没事也经常去帮衬帮衬他。黄少天对喻文州说。
喻文州笑着点头,又问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车票和钱都放好别掉了,最好衣服里面的夹层上缝个口袋……
喻文州你怎么跟我阿妈似的。他拿膝盖顶了他一下。
也不是不放心,就是觉得程序上得这么嘱咐两句。喻文州难得地有点尴尬,摸了摸鼻子。
黄少天吸了一口气说,我还有点事想找你,一是这份花生巷的房契你帮我收着,万一……就归你处理。
喻文州没去接,还有呢?
黄少天抿抿嘴说,我想跟你做一次,就现在。
喻文州笑了,说你回去吧,别发傻。房契我也不能收,你托给街坊的陈阿婆,徐太太,权哥,托给郑轩,宋晓,哪个朋友同事都可以,你信任的人就好,但是不要给我。
他狐疑地问,为什么,难道我不能信任你?
喻文州摇摇头,你不是因为信任我才给我,是因为你中意我。
那既然我中意了你,你也中意我,为什么又不肯跟我做?
“你不要忘了你是为什么走。”喻文州轻声说着,这几句话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回响。
“你是为了去看你没有看过的东西,是为了过对得起自己在世上走这一趟的日子。你不愿年纪轻轻就和我一起避去乡下,现在又要和我做了那些才心安,你不该这样。
“你还没有真正拥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你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我不能掺杂其中。我不知道你这一去能不能回来,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很快就会放弃了你,找一个女仔娶妻生子。这是一个赌,你已经拿命来赌我的感情,我不能向你要求更多。
“你会遇到更多的人,等你觉得看够了,不再向往别处,你再重新考虑。我也不能保证我是不是还会等你,现在你是自由的,我也是。”
黄少天觉得点下去的头有千斤重。
喻文州时时都对着他笑,唯有这一次他看不懂。明天他就上火车了,喻文州看他傻兮兮地过来说这么些话,却好像完全没有生气,也没有痛苦,反而很高兴似的。
这样也好,这样他就可以没有负担地走了。
“你的血是热的,趁它还没有凉的时候,你该去那些地方。”喻文州最后说。
“我明白了。”他扬起下巴,笑得一如既往地骄傲又张扬,“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门合上了,他在楼道的阴影里悄悄握紧了拳头。
状态不大好,很多地方欠铺垫,急着想写小卢(?!),先放着全部完了再修。
很多事情现在写起来都是一股子粉饰太平的味道,真实比文字要惨烈许多,所以不愿详说。
文州的想法见番外长歌。
'喻黄'月半弯(九)
说HE就是HE,什么时候驴过人w
在这章说这种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反正我写的时候脑内BGM都是爸爸去哪儿……
九、燋茶
卢瀚文是在葵田里打着滚长大的,高高低低油绿色的蒲葵叶子下面就是他的童年了。
从记事开始,他就每天看着阿妈坐在小院里剪、晒、焙、削,摘下葵叶葵柄来制扇、制席、制帽、制蓑衣,年复一年,这样的日子好像没有尽头。阿爸不到四十岁,一张脸却是僵的。何村长召集村里青壮年男人开会,他偷偷躲在祠堂后面看,阿爸每每都坐在角落,从不发言,和旁人说话也不敢大声。
他从小机灵,又活泼好动,村里老老小小都喜欢他。何村长有时也单独请他到家里做客,何太太做上一桌子菜,碗里白饭添得满满的。有一天他终于没忍住,问何村长,“阿爸阿妈为什么成天都闭着嘴,不敢出头?”
何村长摸摸他圆圆的脑袋,“你阿爸阿妈有苦衷,不要怪他们。”
卢瀚文似懂非懂地点头,何村长又说,“你还小,现在只乖乖地跟着他们就好,只可惜了一棵好苗子。等你长大了,再看看有没有转机。你长大想做什么?”
他扁了扁嘴,“我不知道。”
他是真的不知道,不知道这样下去,除了养好身体,长大帮阿爸锄田,帮阿妈摘葵叶之外,还能干些什么。
卢瀚文长到七岁上,有一日阿爸从村长那里回来,虽然他平时就是一脸阴沉的样子,那天眉头又皱得格外紧。
他藏在卧房的门后面,听不清完整的话,只听得“膏药旗”“瀚文”“后院”“水缸”几个词,剩下的就只是长长的叹气声,阿妈也跟着阿爸一起锁起眉头。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阿妈就同他说,以后不要出去跑,听到有穿着皮靴的脚步声靠近了,就躲到后院的水缸里,盖上盖子,小心别出声,被发现了是没有活路的,知不知?
阿妈的表情很认真,他只好用力点了点头。
村里人的草鞋布鞋踏在土路上是没有声响的,高筒军靴却不一样。不出几次,卢瀚文就摸清了那些哒哒的脚步声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会来,走了又往哪个方向去。
那天阿爸阿妈都下了地,他在邻居家食过中饭,九月的天高高的,风吹过来清清凉凉。昨天日本人刚刚来搜过一趟,他料想今天大约不会有什么,就拿铁盒装了饭菜,自告奋勇地去地里给阿爸送饭。
还没走出一里远,他就听见了脚步声。那些哒哒声好像从来没有那么近过,一下下仿佛是踏在他胸口上,闷得大气也不敢出,饭菜打翻在地上,他拼命地往葵叶下面躲,声音却越来越近了。
蒲葵陪着他长高,他希望这群伙伴能救他一命。
救他的却不是蒲葵。虽然被捂住了耳朵,还是听到身边爆起了几下利落的响声。
等他从惊惶中睁开眼睛,葵叶的阴影下看不清楚那人的脸,厚实的大手拍在肩上很有力。
“以后小心些。”对方只是这么说着,就往别处去了。
那件事后的第二年,卢瀚文已经养成一听到脚步声就往后院跑的习惯以后的某一个秋天午后,他在厅里折纸青蛙玩,又听到一阵脚步声。
不是布鞋或者草鞋的声音,却也不是重重的军靴声。
这声音很有节奏,不快也不慢,不重也不轻,像下了雨的晚上水珠打着芭蕉叶。
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男人站在门槛前面,背着光对他笑,“你就是卢瀚文吗?”
后来卢瀚文就坐到了村口大祠堂的一间厅改成的破教室里,旁边的人都比他大上三四岁。
那个高个子男人对他说,是何村长荐他来的。村长说这孩子虽小了些,可是脑子聪明,学得快,今后一定比那些大孩子出息。
男人叫喻文州,他跟着学堂里的其他孩子叫他喻先生。
喻先生脸上最常见的就是笑,不温不火,对谁都是一样。眉眼弯起来,看得人心里融融的。
他问旁边长了四岁的女仔,“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厉害。”
女仔托着下巴眨眨眼,“那当然。”
他回到家,跟阿妈说起学堂里的人都喜欢这位喻先生。阿妈少有地停下筷子,掏心掏肺似的说。
“这人不简单。他冲你笑,笑得是真心实意的,不会讹你也不会伤你,却好像留着些什么,摸不透。”
“村里的年轻女仔抱着艾草跟他打招呼,旁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也只点头笑。他对你很好,可也就这样了,进不去心里。这人心里有事。”
阿爸手肘顶了她一下,“当着瀚文面前说这些做咩。”
阿妈于是收了声,卢瀚文却还在想着那些话。何村长说阿爸阿妈都是厉害人精,只是不愿露,他好像有些明白了。
一天下了国文课,喻先生走到他桌子前面说,“晚上来我家食饭好不好?我同你阿爸阿妈说过了。”
卢瀚文撇撇嘴,“你告诉我说过,就一定说过了?我自己去说。”
喻先生笑得直不起腰,“好,你去说。”
他回了家,阿妈奇怪地看着他,“不是说去先生家里,怎么又回来了?”
卢瀚文愣一愣,“哦,先把书本放了。”
他又来到喻文州家里,男人从炉灶前站起身来,“是吧,我又不会骗你。”
他有点尴尬地抓抓头,嘿嘿笑着。喻文州也看着他笑,卢瀚文觉得他今天笑得和平日不大一样。
喻文州指指壁橱,“去把碗筷摆好。”
喻文州看起来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手上却很精细,没一会儿桌上就摆起两菜一汤,清炒藕片,西芹腊味,绿豆猪骨汤,颜色明明白白。
卢瀚文看得食指大动,吃了一碗又从高椅上跳下来,“我还要一碗。”
喻文州笑着,又给他盛了一碗汤。
他忽然问,“瀚文,你长大想做什么?”
卢瀚文还没说话,他就自问自答起来,“你才八岁,没主意也是正常……”
他想起了一件事,仰起脸说,“我想去当兵。”
喻文州的手不动了,笑容僵在脸上,像梵婀玲的乐声被生生掐断,只留锯木般的尾音。
他也跟着沉默了一会,等乐声再奏起来,才敢继续同喻文州说话。
喻文州听他说完原委,托着腮说,“我觉得很好,只是你阿爸阿妈未必答应,他们还是想你做个本分人。”
卢瀚文又想起什么似的,往前探了探身子,大着胆子问,“先生,何村长说阿爸阿妈有苦衷,你知不知是怎么回事?”
喻文州摸了摸他的脑袋,半晌才说话,“你还没到知道这些的时候,等他们觉得时候到了自然会说与你知。”
卢瀚文点点头,又问,“那你说,要是我阿爸阿妈不答应,我还该不该去当兵?”
喻文州戳戳他的左胸口,“等你知道那些了,你再问这里。”
卢瀚文十三岁那年,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有人从外头来村里,一脸兴奋地跑到何村长家,大家才知道日本人已经退了。
阿爸阿妈也难得喜形于色,何村长在祠堂前摆了流水席,全村人聚在村口唱唱跳跳,舞起醒狮,高兴得不得了。
他也跟着大吃大喝了一遭,吃到一半,阿爸阿妈说要带他去敬酒。
先敬了何村长夫妻两个,又敬邻居家,最后才领着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