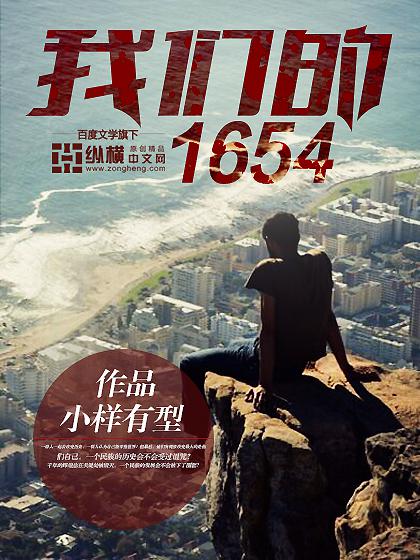家丑1-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反。虽说她亲眼目睹了赵先娥一家和沙吾同遭受迫害的惨状,但让她同王贵桥怒目相向,她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陈小焕他们只要求她能把市委机关的人马稳住,保持中立就行了,不要求她齐秋月去冲锋陷阵。可是,郑连三领一批人马造反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保王贵桥,正同陈小焕他们的观点对立,机关里的人纷纷倒戈,齐秋月的红革会眼看就要被吃掉。沙吾同领着他的串联小分队就来市委机关声援,准备也像在沙家湾那样让他郑连三这个工作组长向红一中革命小将下跪,从而刷他一脸黑,让他的“八。一八”从此抬不起头来。那天,两个老同学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候见了面,不由感慨万千。齐秋月先关心他的身体。沙吾同晃了一下胳膊,说:“能动了,就是不太灵活,还不能随心所欲。”齐秋月的眼睛就湿了,说:“你受了大罪了!”沙吾同说:“难为你在那种时候还敢想着去看我。夏老师都给我说了。”齐秋月这才说起机关里的斗争形势,沙吾同说:“你从小就心肠太软,这造反可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血淋淋的啊!哪里像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学毛著写心得一样。”说得齐秋月没法接腔,看看言重了,他换了话题,问起齐老师受冲击了没有。齐秋月说:“乔端县文教局有一派保他,可不是红造总的,是郑连三那一派。”沙吾同笑笑说:“一家两派啊!”这时几个随来的学生耐不住寂寞,竟跑到郑连三办公室门口刷出“菊乡头号保皇派罪该万死”的大标语,要揪郑连三向一中学生认罪,引起磨擦。这一批学生娃的手脚都是指点江山惯了的,怕谁?马上冲进办公室,找不见郑连三,就一阵猛砸,油印机,桌椅板凳都被砸个稀火巴烂。美其名曰:砸老保有理。齐秋月沙吾同赶来时,已经乱成一锅粥。红一中的小分队喊:“郑连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该万死!”机关的人喊:“沙一方的臭孙子,不许翻天!”机关门卫同郑连三一派,马上以破坏公物扰乱治安为名把红一中学生及其黑后台沙吾同挡在市委大院,逼进一间地下室关了起来。齐秋月也让人堵在她的打字室,不许挪动一步。
郑连三到地下室去看沙吾同他们。门一开,沙吾同就说:“放我们出去!你不能重蹈覆辙,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恶,镇压红卫兵造反派。”看郑连三无动于衷,他就大骂:“你个狗东西!”郑连三笑笑说:“你骂人可不像个老师。只是——况且这样教唆年幼无知的小青年搞犯罪活动,可不是当老师的职责。”几个学生马上骂道:“郑连三你看清了,老子们都是你在一中打的小邓拓。你他妈的溜得快,要不这笔债早该清了。今天就是来向你讨债来的,你快快给老子们跪下,免你一死。”郑连三没有回骂,他宽宏大度地笑笑,说:“我同你们的沙老师说两句话,你们给我个机会吧!”不等小将们再说话,就走到沙吾同面前:“我知道你恨死了我们郑家,可我也恨死了你们沙家。请不要把我们两家的恩怨搅到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里去,搅进去了,也不要把你的学生再带进来。这是其一。其二,我提醒你一句,毛主席有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如今的形势是,东风劲吹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你还想吹股冷风,行吗?你这个操纵一中学生犯罪的反革命黑手,陈小焕就是让你引入歧途的,你还要把其他的同学们都往死里拖。你应当深刻反省。”这时,几个学生对他又是一顿臭骂,他笑着说:“你们应当骂他,他是披着老师人皮的狼,不要认错对像。”沙吾同说:“我记得,在革命小说《红岩》里,徐鹏飞对江姐也说过类似的话。”说罢他嗤鼻一笑,傲然地立在郑连三面前。郑连三又笑了,说:“好啊!当罢了华子良,还要当当江姐。真难为老同学这么想。你把自己先变成女人再说吧!”几个小青年就喊:“骟了他!”“他们沙家就不是好种,让他们断子绝孙!”郑连三用手制住了他们,说:“让他自我反省吧!”走了,留下这几个青年看管他们。这几个人安静了一小会儿,就又拿沙吾同开心了,说:“亏得刚才没动手,要骟了你,你咋喝齐秋月的刷锅水?”另一个说:“刚才他就把学生娃们打发到前院,他俩在屋里热乎哩,让咱造反战友堵在屋里抓来的。”那一个又说:“他们这种人就是孬种,他那反动司令爷爷就是这样,祖传的坏东西。”他原是闭了眼睛的,不想正眼瞧他们,在学生面前他不能表现得太粗鲁,听听这样糟蹋人家齐秋月和自己的老祖先,他发火了,骂道:“放你妈的屁!你他妈祖奶奶起,都是男盗女娼!”这么你来我往几句,这几个小青年就把他好一顿收拾,几个学生来护老师,他们就连带把小分队的人也一锅烩了。
这时,齐秋月心急如焚,她却不能走动半步。她心里也很后悔,又骂郑连三,他竟敢派人把她软禁起来。她对看守她的人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样限制人身自由犯法?”看守也是郑连三从街道上大联委的下属组织找来的,街道上早就流传过齐秋月的绯闻,这一回他们可算是饱了眼福。这个美若天仙的女人同他们说话,他们高兴极了,又笑了,说:“先别说自由不自由的话,都说你是菊乡的形象天使,今日一睹芳容,还真名不虚传。”又一个说:“别胡说那没滋没味的话,齐秋月同志如今是学毛著标兵,让她给咱们背背毛主席语录吧!”齐秋月真的给他们背了起来,还给他们讲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想让他们认清当前形势和郑连三的嘴脸。这些人听了,只是哧哧笑笑,就是不把她的门打开。她才知道对牛弹琴了。就不再吭声,坐桌前,用梳子把乱发梳着,想着应急之策。
也怨她心肠总是太好。郑连三造反时,曾对齐秋月说:“咱们老同学各树一帜,都是保护革命领导干部王贵桥,你暗保,我明保,也算一唱一和吧!希望不要伤了和气。”齐秋月就没有在意。谁想王贵桥跟武装部政委是武工队时的老战友,对郑连三和郑运昌的家史也有记忆,对郑运昌之死也耿耿于怀。两人通了气儿,武装部就代表解放军支持了郑连三他们的“大联委”,把齐秋月闪到一边。齐秋月的“红革会”一下子就有上百人发表声明,退出红革会,申请参加郑连三的大联委。齐秋月快成光杆司令了。红造总眼看市直机关就要成了郑连三的一统天下,也很着急,无奈齐秋月不是那种能踢能咬的主儿,再怎么努力,也撑不起这一方即将塌下的天地,沙吾同就带着他那战无不胜的串连小分队杀了进来。
齐秋月心里在骂着自己:“你一个女孩子家,造什么反。是不是学习毛著标兵的光环让自己有了权力欲望。”她深感不安,如果沙吾同再让郑连三折磨得脱层皮,那她就会愧疚一生。
怎么办?这个消息得赶快送出去。
第二卷第六章隔墙姐弟(3 )
猛然,她眼睛一亮。赶忙写了个纸条,塞进打字腊纸筒里。乘人不备,隔窗扔到大街上。她想,不管是大联委还是红造总的人捡了去,沙吾同等人被关押的消息敞出风去就行。
郑连三自从跟着大伯郑运昌在武工队禁闭室见过姐姐一面,尔后再也没有见过姐姐,姐姐后来又拉起杆子当刀客一事,一直是他档案袋里不光彩的一页。这当然影响了他的进步,再加上他同齐秋月那档子事,直到四清开始时,他还只是市委办公室里一个普通的秘书,管管杂务跑个腿儿。王贵桥调来后,才算有人正眼看他。两人也多了个话题,说起武工队的事,两人都感慨万千。王贵桥说:“你姐姐也是个烈性女子,咋能走上了那条路。听说后来还同剿匪小分队公开摊牌,要求放我出狱,难为她的仗义。哪里知道江湖上的规矩不能同革命原则相提并论。”郑连三说:“党对她也算宽大,听我大伯说,组织上一直想劝她投降归顺。后来她也算明智,放弃了抵抗。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是被她手下杀死了,还是被沙一方的残余势力杀死了,不得而知。”王贵桥又问:“就因为这一点影响了你的进步?”郑连三说:“我本人有好多缺点。不过,有这个因素。”王贵桥说:“那时你还只是个孩子哩!”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郑连三当然要保王贵桥,要保王贵桥,就必须吃掉陈小焕他们的红造总。于是想通过“新一中公社”来挖掉红造总的老根——陈小焕他们的“红一中公社”。这一天他终于逮住了杀进菊乡一中的机会,谁想,他让红一中的尖刀军给抓住了。他窝囊透了,心想,这一番折磨逃不掉了。能在折磨中经受考验,他在组织中威望会更高,在军代表眼里形象也会更好,将来进入三结合担任主要职务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那样,他郑连三就不会像前几年这样窝囊了。
他要让人们知道,他郑连三原本就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劳动英雄的后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一个学生拿把尖刀在他眼前晃了晃,问:“这次围攻革命造反派,是你预谋策划的,是吧?”他说:“不是,是你们的沙吾同坏分子干的,他先到‘八。一八’搞打砸抢,向我们挑战。我们这是自卫反击。”另一个学生上来给了他一鞭子:“跟他啰唆什么?这次围攻,他就是总指挥。”他说:“我不是。我是革命造反派,真正的造反派。”学生说:“你也造反?你是菊乡头号保皇派!该死!”抽了他一鞭,又问:“王贵桥是你黑后台,他给了你什么黑指示?”他不答。“是王贵桥支持你围攻革命派?是吧?”他说:“不是。你们颠倒黑白。”这一下,尖刀军的学生们火了,一皮鞭抽在他的脸上,他“哇”一声大叫,用手捂住了脸,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又是一皮鞭,又是一皮鞭。有人大骂:”你这个狗东西,你姐姐是大土匪,你迫害革命师生,罪该万死。“”据揭发,你和你大伯假扮开刀讨饭,给山上你刀客姐采点,有这事吧?“郑连三不回答,再问他啥,他就跟哑巴了一样。皮鞭抽在他身上,巴掌打在他脸上。不一会儿,他就昏死过去。一盆水兜头浇下,他又醒了过来。就在这时,有人大叫:”陈小焕受伤了,前方吃紧,尖刀军,快上啊!“这群学生忽地一下子全跑走了。一个学生把郑连三捆绑结实,不管他死活,提了提绳子,一拉,拉到老余床边,绑到床腿上,叫来老余,交代说:”这可是杜聿明级战俘,看紧点。“走了。
这次武斗,陈小焕受了轻伤,沙吾同却不知让人家押解到何处。同学们马上想到用郑连三换人。但是,当陈小焕领着同学们来到老余屋里找人时,郑连三不见了。问老余,老余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门锁得好好的。
当初,老余把门锁了,拿着钥匙,来这边屋里,想同陈小焕母亲说说话。谁想陈小焕母亲正浑身发抖,呼吸急促,病得不轻。老余问:“咋啦?大嫂!”赵先娥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眼看病人就要有危险,老余把钥匙顺手往桌子上一丢,去倒水,伺候她喝了一口水,扶她躺下,问她可好一点,赵先娥无力地点点头。老余说我去叫校医来,就急急忙忙出去了。赵先娥缓过气来,不由在心里呼唤:“天哪!这是哪辈子遭的罪孽啊!”以前,小焕骂工作组时,他以为那个姓郑的是别人,今天学生们的骂声里提到他姐姐是大土匪,这就证实了隔壁这个工作组长就是他们郑家的小三儿。天哪!她脑子里不断闪现弟弟那稚气的脸。那时,他才五岁吧,父亲生意上不顺当,要回四川老家,临走,弟弟拉着姐姐的手哭着说:“姐,我不走,我跟姐姐一起上学。”姐姐说:“你还小哩,等长大了,可上学。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有本事了,挣大钱,咱爹就不用起早贪晚做生意了。”弟弟说:“不,我挣钱了,咱们还来菊乡开药材行。”那稚嫩的声音,让当姐的好生安慰。可是弟弟后来再来菊乡却是陪着爹娘来求沙一方。父母双亲被杀害了,弟弟也险些丢了性命。而后相见,竟是在解放军武工队的禁闭室。
今天,这个令她百般思念的弟弟就在隔壁,而且正在遭受折磨。也不知道女儿小焕他们会怎样处置他。她的心里似油煎,真想到隔墙问一声,又怕小焕和她的那些同学知道了产生怀疑。一旦连带出自己那一段趟刀客的身世,她自己完了是小事,小焕摊上了这么个土匪老娘,小弟摊上这么个土匪姐姐,他们一辈子的前途就都完了。
隔壁屋里有些细微的响动,一会儿传来微弱的呻吟。这一声声呻吟虽说微小,但却似利剑插在心头,她急忙又侧起身子喝了口茶,看见了老余放在桌子上的钥匙,眼前似乎为之一亮,但是,随即又熄灭了。不能啊,这不是出卖女儿吗?女儿受了多少磨难才有了今天。这个郑连三,他不是那个哭着喊叫“姐姐”的弟弟,而是残酷迫害女儿的坏人,就是今天,他还起心要把女儿这一派人打垮。当初打女儿小反革命,把她开除回家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就是他。他是工作组长,小焕提起他就骂他是刽子手,不得好死。如今小焕翻了身,站到人前了,他还想把她再踩在脚底下。这个狗东西,他这个人就是那反动路线的代表。运动开初自己站桌子,被绑着游乡,也是他们那一条路线上的人干的。我能给他们讲善心,讲姐弟情?想着,她就咬了咬牙,让他这个人和他那个路线受罪吧!
但隔壁那个男人的呻吟委实像尖刀剜着她的心。如今世上只有他这一个娘家根苗了。他要有个三长两短,老郑家这一支就断了后。他是为了替她报仇才同大伯流落到菊乡的呀!他们开刀讨饭,险些毙命,活到今天,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也真是不容易。不知道成家了没有,有没有孩子,如有了孩子,她就是姑姑了。当姑姑的能对娘家人见死不救?看这仇气越斗越深的架势,红一中非要把他整死不可。弟弟,一奶同胞的弟弟,爹妈死了,听小夏说,沙一方的狗孙子回沙家湾把大伯也整死了,娘家就剩这一个亲人了……就这一根独苗了……
一边是女儿,他们应当胜利,他们应当翻身,他们应当扬眉吐气。但是,这个郑连三反对他们胜利,反对他们翻身,反对他们扬眉吐气。当妈妈的就应当站在女儿这一边,为他们的翻身,为他们的胜利,为他们的扬眉吐气,不能出力流汗,不能冲锋陷阵,不能摇旗呐喊,但也绝不能从后边放走他们的对手。她这个妈妈应当这样当。
第二卷第六章隔墙姐弟(4 )
一边是弟弟,他应当逃掉,他不能死。但却被禁闭在隔壁。她不能为弟弟遮挡皮鞭拳头,她也应当把他人放掉,让他躲过这一难。她是姐姐,应当为弟弟的生命负起责任,她如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条件,这里的一串钥匙,这里边就有一把钥匙系着弟弟的生命。她应当把弟弟的生命解救出来。
她好为难啊!她心里在呼唤着:天哪!你咋能让我们老郑家的人自相残杀呢?你咋让我这个当妈又当姐的女人遭受这种折磨呢!我遭受折磨,为难死自己也不能向外人露出一点点真情。她只有把这一切闷烂在肚里,直到老死……
她扑通一声,栽倒了。
她不能倒下,没有太多的时间了,老余就要领着医生回来了。医生是来救命的。她的命有人来救,值钱。弟弟的命也值钱啊!那是老郑家留在菊乡的一条根啊!可弟弟的命谁来救呢?
她拿钥匙的手抖动着,抖动着,终于打开了老余的门。灯光下,她看着这个男人的脸,脸上,像是有弟弟当年那种稚气流露着,再一看,竟是一脸血迹,他的手被反绑着,侧身靠在床腿上。听见响动,他头也没有抬,说:“放我走。”声音很微弱。她说:“放你走?”声音也很小,像是发问,又像是感叹。不过他还是听到了,微微睁开眼,看见一个女人的脸,他说:“放我……”女人把他绑着的手解开,她的手抖得厉害,她打开那串钥匙链上的一把刀,刀光一闪,他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说:“你要杀我?”她背过脸,艰难地说:“我就想杀你,可我要放你走。”他问:“你是谁?”她说:“我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那一段土匪刀客生涯不仅不能让女儿知道,也不能让这个弟弟知道。她说:“我是放你走的人。”用刀把绳子割断,“你快走。”她背向着他,站在黑影里,又说:“快走!”郑连三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他说:“留个姓名吧,日后定报大恩。”扶住床腿站了起来,挪到门口,扶住门扭回身来,想看看这个救命恩人,可他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女人的背影。他说:“我谢谢大姐!”听见这一声“大姐”,赵先娥差一点就答应一声:“哎——我是那个苦命的姐姐!”但她没有说出一句话,她只不过向他摆摆手,说:“为人多做好事,别伤天害理。”
郑连三走了。
赵先娥又把门锁上,回到这边屋里,喝了口水没有咽下去,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头撞在桌子角上,碰破了,血立即顺脸流下来。杯子倒了,水顺着桌子向下流着,滴在她的脸上,和着血水,顺脖子浸湿了胸前的衣服。
沙吾同下落不明。
郑连三逃跑了,逃得莫名其妙。
妈妈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头上有打破的伤口,在流血。
陈小焕马上断定,这是“八。一八”和“新一中公社”的人,打昏了妈妈,抢走老余的钥匙,救走了郑连三。“血债要用血来偿!”她一面把妈妈安顿好,一面调兵遣将,追捕郑连三。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沙老师和被抓的战友。
这天夜里,我正在语文教研组写大字报,前院有人用石头瓦砾对撩时,我听见了呐喊声。正要去看个究竟,门外进来几个学生,手里拎着大刀,拦住我,说是陈小焕派他们来保镖的,要保护革命老师,尔后就像门神一样一边一个立在外边。直到他们要组织大反击,这两个忠实的保卫者才被叫了去。我马上锁了门到前院用手电一照,天哪!遍地砖头瓦块,还有折断的棍棒、撕破的衣服片、纸屑等等。还有学生“嗵嗵嗵”地向大门外跑去,有的又跑回来,一派紧张恐怖气氛弥漫了校园。看来更大的武斗打到大街上了。我忙拉住一个女红卫兵,